
穆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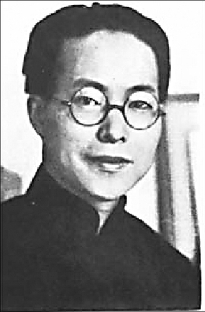
沈從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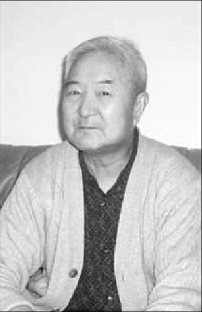
柯原
1947年9月20日的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上,刊出了這樣一則啟事:
“有個未識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喪事情形困難,我想作個‘乞醯’之舉,凡樂意從友誼上給這個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點困難,又有余力做這件事的,我可以為這位作家賣二十張條幅字,作為對於這種善意的答謝。這種字暫定最少為十萬元一張。我的辦法是凡是要我字的,可以來信告我,我寄字時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給那個窮作家。這個社會太不合理了,讓我們各盡所能,打破慣例作點小事,盡盡人的義務,為國家留點生機吧……”
這個充滿愛心,誠心謀事,解人困境的“啟事”發布人,是該周刊的主編人沈從文。
支持“未識面的作家”
1946年8月,沈從文從抗戰時期居留的昆明回到北平,繼續在復校后的北京大學任教。10月,他接受了天津《益世報》的邀請,出任該報“文學周刊”副刊的主編。
第二年的夏天,沈從文陸續收到一個筆名“蘆葦”的作者的詩歌。詩歌頗富激情,沈從文喜歡,便在7月19日,刊出了這位作者的《飛吧,我的心!》等詩作兩首。這一下子點燃了詩人的熱情,他又不斷地向《益世報》投稿。接下來的幾個月,幾乎每月都有這位詩人的詩作刊出。一些詩稿,沈從文還推薦發表在北平的《平明日報》“星期藝文”副刊上。這家報紙的副刊,也是由沈從文主編的。不刊用的稿子,沈從文還負責地退回。退稿信,沈從文親自來寫,有時還附出具體意見。這使得詩人與這位編輯先生親密熟悉起來。
這位“蘆葦”,就是后來以詩歌聞名於世的柯原。柯原當時隻有16歲,是天津“河北高等工業學校”的一名學生。他所學專業雖然是化學工業,可卻喜歡文藝。在艾青、田間、綠原、李季……詩人詩歌的閱讀中,柯原開始了新詩創作。據他后來回憶:當時年齡小,有闖勁。買不起稿紙,找些邊角白紙,自己刻蠟紙,在學校油印機上印出,成了自己獨特稿紙。詩作發表,有時收不到樣報,就在傍晚時,拿把小刀,在閱報欄上把自己的稿子割下來。盡管他一個編輯部的人也不認識,卻敢於寄稿。也幸好遇到沈從文,他第一次寄稿即獲發表。
幾個月之后,柯原與時常通信的沈從文就有了一種特別的信賴感。就在此時,柯原當小職員的父親因年老被裁失業,隨即又得了急性肺炎。當時可以救急的西藥極貴,一小支消炎用的盤尼西林(按:今名青霉素),竟需要十幾萬法幣。治療未久,父親去世。期間花銷及喪事費用,使他家欠下一筆債務。當時柯原家隻有姐姐一人當小學教員,菲薄的薪水根本不足撐起這個家庭。看到母親和姐姐的愁苦狀態,16歲的柯原便向沈從文寫了一封信,說明家境情況,並提出想預支一些稿費的請求。
當時的知識分子,生活一般都不寬余,所以正式工作之外,總要多處兼課兼職,以補家用。沈從文自己當時除在北大任教,同時還擔任數家報紙文學副刊編輯,便是這種狀況的反映。接到柯原的求助信后,沈從文萬分焦急,但他知道,以當時柯原的知名度和文章,是很難獲得報紙預支稿酬的。而自己又實在拿不出一筆錢,來支持這位“未識面的作家”。於是,他便隻能試著用自己手中的筆,來給予柯原一些實際、真正的援助。這樣,就有了那則“啟事”。
難以忘懷的情分
在當時,文人一般很少賣字。因為在人們看來,這實在算不得什麼正途。那段時間,沈從文日子也頗為困窘,可他就從未想過為自己賣過一張字幅。但沈從文是一個善良熱情、慷慨好義之人,在這救助乏術的特別情況下,他動用了作為文人的最后一點點資本。
沈從文的這則啟事,還有一點令人感懷:他並沒有在這裡公布這位青年作家的姓名。而隻要求買他字的人寫信來,在自己寄字回去時,才告訴青年作家的地址,請買字者寄款過去。他不願意公開這位作家姓名,是免得他和家人受到其他無謂的干擾。這表現了沈從文深入知世又良善的心性。
“啟事”刊出后,因為沈從文著名小說家的名氣,加之許多人都聞知他的一手章草寫得確實漂亮,陸續便有人致信,將自己對字的規格、內容寫上,由沈從文書出,寄回時再告訴柯原的地址,以便寄款幫助。
從后來接到寄款的柯原家所知,當時樂意花錢買沈從文字的,也並沒有什麼大款闊佬,多是一些善良的普通人。他們都實誠地按地址寄去了錢款,有的還寫信表達親切問候。柯原后來回憶,他家陸續收到了寄來的款項有20多份。用這筆錢,他家終於還清了債務。他當然更清楚:“這是在當時情況下,沈從文老師對一個無名詩人所能盡到的最大限度的捐助了。”這樣的情分,自然不能忘懷。后來許久,柯原的母親還“一直叨念和祝福這位沒有見過面的好心腸教授”。
可快速發展的時局竟使沈從文和柯原幾十年都沒能見上一面。當時沈從文在北京大學,柯原在天津,距離雖不甚遠,可1948年冬天,進步的柯原越過國民黨封鎖線,到解放區入華北大學學習。1949年3月參軍,南下。再往后忙於各種工作……便與沈從文中斷了聯系。
見面的激動
在部隊的幾十年間,柯原寫下了大量富有南國氣息的軍旅詩作。因為特別的情調,獲得了讀者廣泛的喜愛。
上世紀80年代初期,報刊上開始報道國外對沈從文作品的評價和研究情況,國內一些出版社已經出版或正准備出版他的作品,見到這些消息,柯原也很高興,他便給沈從文去信,報告自己的情況,並附了兩本詩集,算是給當年鼓勵他的長者交上的一份“作業”吧。
接到柯原來信,沈從文也很高興。雖然事情已過去數十年,可提起筆,沈從文還是將柯原作為一個可以深談的友人:“你在軍隊中搞宣傳工作,用新詩作武器,必比較容易建功。且可能還有機會各處走動。據我私見,除正常工作外,如還有余暇時間可用,最好試寫點散文,或通訊報道性作品,肯定會比一般作家臨時短期在某地某處採訪作的文章扎實而深入。”這樣的看法,很值得寫作者,尤其寫詩者的注意。
收到沈從文這封親近的復函,柯原自然很高興。1980年夏天,在赴北京參加征文授獎會議期間,他趕到沈從文家,看望這位數十年前幫助過自己的文學長者。見到沈從文,柯原自然談起當年沈從文賣字救難他們一家的義舉,不料老人已經記不起這件事了。也許,在沈從文的記憶中,並沒有將自己所做過的好事留存心頭。
柯原眼前的沈從文,已是一位文物學者:“自然,沈老最有興趣的,還是談他的古代文物研究。建國后他從事這項工作已經三十幾年了,談起來如數家珍,滔滔不絕。實際上他的家中也是一個小小的古董陳列館……我望著這滿屋的書籍、字畫、古董、資料,這裡的一切都是第一次見到的。既陌生新鮮,又有一種一見如故的感覺。這間小屋給了我一種親切感。”
1988年5月,著名作家沈從文逝世。柯原馬上寫出《淡淡的色彩和一縷清香》一文,悼念這位並沒有直接教授過他,卻給了他更多人生關懷和教育的老師。他在文章結束時這樣說:“沈老曾經說過:‘我和我的讀者都行將老去。’這話頗有些傷感而撥動人們的心弦。但我認為沈老的文章是不會老去的,是有久遠的生命力的,從沈老的作品近年來紛紛在海內外出版來看,它已經擁有了一代讀者,還將贏得一代又一代海內外的讀者。”
的確,沈從文的作品顯示出他久遠的生命力,沈從文為幫助柯原而主動賣字的故事,是值得我們珍視和記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