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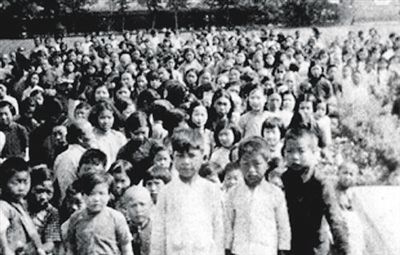
安全區內難民營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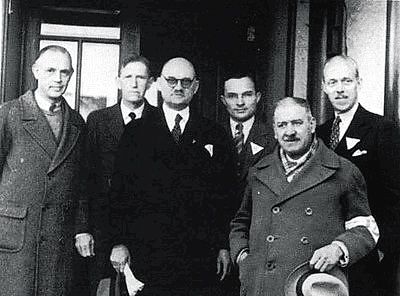
南京國際安全區和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部分成員,居中者為拉貝。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攻佔南京。從這天開始,南京恍若與世隔絕的人間地獄,侵略者制造了一場震驚中外的大屠殺,30萬同胞慘死於敵人的屠刀之下。也就在這時,有23名西方僑民自願留在南京並主持設立了“南京安全區”(又稱“難民區”),籍此保護了近30萬中國人。今年的12月13日是我國的首個國家公祭日,在祭奠那些死難同胞的同時,那些曾幫助過中國人的外國友人也同樣值得紀念。
“安全區”的設立
1937年11月,日軍攻陷上海后大舉西進,直逼南京。為保護本國國民,各國使館在8月中旬即開始撤僑,但其中有23人拒絕了本國政府的救援而毅然留在南京。這些人主要以教師、傳教士、醫生為主,他們在南京已經生活多年並以“老市民”自居,對這座城市和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
隨著戰爭的一步步迫近,留守南京的他們也不是不知道其中危險,但心中的道德感最終戰勝了恐懼。如德國西門子駐南京辦事處主任、后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的拉貝在日記裡說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能離開嗎?我可以離開嗎?我不能!富人們跑了,剩下的全都是窮人,他們不知道要去哪裡,而且非常多。我決定我要幫助他們。如果說我一點都不害怕,我是在說謊。……我也不想為了公司或個人的財產而拿我的生命冒險,但這裡存在一個道德點,作為正直的漢堡商人,我至今都無法逾越它。”
金陵大學鼓樓醫院的美國醫生威爾遜也在家信中說:“如果美國人離開,醫院將會被迫關閉。我覺得我們不能離開,我們要抓住機會,盡力地提供幫助……”戰爭爆發時,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與全家正在日本度假,后來他沖破重重封鎖隻身回到南京。與他們一起堅守的,還有牧師米爾斯、馬吉、費吳生,金陵大學教授史邁士、裡格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代院長魏特琳,鼓樓醫院代院長特裡默,德國工程師克勒格爾等。
據曾任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干事的杭立武先生回憶,當時為解決南京戰事爆發后的難民問題,其約集了在南京的一二十外國人,准備按上海設立“難民區”的先例成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以對可能的難民實施人道主義救援。貝德士、馬吉等人對此表示同意,最后由拉貝出任委員會主席,總干事一職最初由杭立武擔任,但后者因為要護送文物西遷而改由貝德士繼任,總稽查由馬吉牧師兼任。
國際委員會劃定的“南京安全區”以美國駐華大使館及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神學院、金陵中學、鼓樓醫院等教會機構為中心,佔地約3.86平方公裡,四面以馬路為界:東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漢中路,西至西康路,界內分設交通部大廈、華僑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學等25處難民收容所。與此同時,委員會又在“安全區”內發起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由馬吉牧師任主席,魏特琳、威爾遜等人為委員,兩會密切合作,以盡可能地救助戰爭中的傷病員。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立后,中國方面給予了積極支持,南京市長馬超俊下令將3萬擔大米、1萬擔面粉及一些食鹽撥給“安全區”,同時還提供10萬元現金及450名警察以維持秩序。此外,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張群將寧海路5號私宅提供給國際委員會作總辦公處,首都衛戌司令長官唐生智也應國際委員會要求拆除了“安全區”范圍內的軍事設施,並於12月7日下令所有軍隊一律撤離“安全區”。
對國際委員會的建議和呼吁,日方的表現驕橫而傲慢。最初,國際委員會通過美國大使館的無線電台將設立“安全區”的建議發往駐上海日軍當局,但后者不予回應。之后,國際委員會通過在上海創設難民區的法國神父饒家駒將“南京安全區”的地圖交給日方司令官,對方先是自稱“知道了”﹔后又冷淡地表示,“難民區內倘無中國軍隊或軍事機關,則日軍不致故意加以攻擊”。
“難民營”裡的求生
1937年12月9日晚,就在南京即將城破之時,國際委員會向報界發送專稿,呼吁居民在空襲與炮擊時盡可能進入防空洞或地下室﹔而且,戰爭期間沒有任何地方是絕對安全的,“日本人從來沒有保証過,不對我們的安全區進行炮擊或轟炸”,“日本人僅僅保証在安全區內不存在中國士兵和軍事設施的前提下不蓄意進攻安全區。”最末,國際委員會公布了救護電話及火情電話,以備不時之需。
從12月初開始,一些家園被毀的市民即開始涌入“安全區”內的收容所﹔隨著南京保衛戰的一步步失利,成倍成倍的難民們更是像潮水一般涌入“安全區”,最初的收容所不敷使用,多數房間要擠上二三十個人,彼此才能擠擠挨挨地躺下來。南京淪陷后,更多的市民在日軍的淫威暴行下匆忙避入“安全區”,這時不要說收容所,就算露天操場也都擠滿了難民。據記載,“安全區”的空地及馬路上建起了數千個蘆葦棚子,“整個難民區其實已成為蘆席棚的世界”。最高峰時,“安全區”內的難民總數可能達到30萬人。
在這樣的一個嚴冬,在如此恐怖的環境下,如何讓這幾十萬人生存下來無疑是一大難題。所幸的是,國際委員會在“安全區”設立之初即未雨綢繆,其不避艱險地“將米一萬擔,面粉一千袋運入難民區”,這使得難民生活有了初步的保障。隨著難民人數的不斷增多,“安全區”內的吃、住、取暖都成為大問題,而在日軍的肆虐之下,“如無外國人挺身而出,和日本兵抗爭,簡直什麼都不能搬動,甚至裝了米的卡車也不許通行。”
為此,委員們不都不各司其職,有的負責找米送米,有的負責找煤送煤,不辭辛苦,以盡最大可能保証難民們的基本生活。而另一邊,日軍為使“安全區”崩潰而百般刁難,米煤供應困難重重。經一系列的艱苦交涉與談判,日方才於1937年底答應出讓大米5000袋、面粉10000袋及600噸煤,但數日后,當委員會會計克魯治前往接洽取貨時,日方卻又借口須由偽自治委員會主持分配而拒絕出讓以上物品。幾經周折,“安全區”才從日方手裡接收大米2200袋、面粉1000袋,稍解燃眉之急。為此,委員們也與難民們同甘共苦,一向吃面包的他們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和難民一樣喝稀飯,以盡可能節約糧食。
並不安全的“安全區”
城破后的南京,遍地都是炮火、血跡與廢墟。為體現人道與中立、去除政權色彩,“安全區”內改懸挂五色旗並以裡圈加紅十字圖案作為“安全區”徽章。在這個流血的季節裡,也許隻有這裡,難民們才能尋覓到一點點的安寧。
但是,“安全區”的安全只是相對的,在這裡,日軍同樣有著各種殺戮、強奸、劫掠、縱火等暴行。12月19日,牧師馬吉在家信中說:“過去一個星期的恐怖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我做夢也沒想到過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蠻。這是屠殺、強奸的一周。我想人類歷史上已有很長時間沒有發生過如此殘暴的事了……日本兵不僅屠殺他們能找到的所有俘虜,而且大量殺害了不同年齡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獵殺兔子一樣,許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隨意殺掉。從城南到下關,整個城市到處都是尸體……”
一些已解除武裝並避入“安全區”的中國士兵,日軍同樣不肯放過,其強行闖進“安全區”並將之集體殺害。目睹此景,牧師費吳生痛心疾首地給友人寫信說:“我們忙著解除他們的武裝,表示他們繳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們失信了!不久他們有的被日軍槍殺了,有的被戳死了。他們與其束手待斃,不如拼命到底啊!”
“安全區”內的強奸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國際委員會副總干事費吳生就表示,“單以金陵大學職員家庭以及美僑住宅而論,我就有關於一百次以上強奸案的詳細記錄以及約三百次強奸案的確實報告。”類似的記載與報告在《南京安全區檔案》中比比皆是,日軍在強奸婦女時均以武力脅迫,如有人阻攔反抗,即行凶殺人。至於其他種種暴行,更是舉不勝舉。
在救助難民的過程中,委員們也經常遭到日軍的威脅甚至人身傷害。如貝德士即被日軍士兵用手槍威脅﹔農藝學教授裡格斯在阻止將平民帶走時遭到日軍毆打﹔威爾遜醫生也在信中說,自己“差一點被槍殺了”,其他人如拉貝、魏特琳等,都無一例外的有類似遭遇。在這樣危險的環境下,他們仍極其秘密地保護了國民黨軍的幾名高級將領,如第72軍軍長孫元良被魏特琳隱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女難民中,教導總隊參謀長邱清泉被貝德士藏在金陵大學管理大樓最頂層密室﹔教導總隊第二旅參謀主任廖耀湘被辛德貝格藏在江南水泥廠的難民營中,這些人后來都被安全送出南京,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1938年1月底,日軍當局聲稱已經恢復南京城的秩序,強迫“安全區”內的難民還家。2月18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被迫改稱“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最后一批難民營於1938年5月關閉。至此,“安全區”的工作基本結束。
在“南京大屠殺”這場史無前例的慘劇中,“安全區”或許是唯一能讓人感到不徹底絕望的一幕。在不到4平方公裡的范圍裡,23位西方僑民冒著生命危險默默地反抗著日軍的殘酷暴行,最多的時候,他們曾護佑過近30萬的中國難民,其“勇毅、大公無私、熱誠及不辭赴湯蹈火來拯救難民的決心與精神”,不愧為南京“活菩薩”、“守護神”的稱號。(金滿樓)

| 相關專題 |
| · 地方要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