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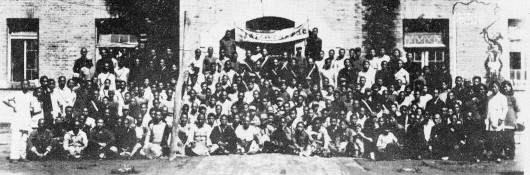
渤海公校歡送部分學員參加軍政學校學習時的合影

1938年9月肖華率部抵達樂陵縣城,受到當地萬名群眾的熱烈歡迎

冀魯邊區的戰士在表演文藝節目
1938年。
7月初的一天清晨,張一然隨身帶上槍彈,獨自從河北省南皮縣董村繞路到慶雲縣,然后轉身由東向西走來。
9月中旬,仉鴻翰謹記哥哥仉鴻印的叮囑,離開家鄉河北省鹽山縣仉小庄,跨過鬲津河由北向南走來。
10月5日,李光遠從寧津縣起身,一路穿村繞巷由西向東走來。
春節剛過,呂本支帶領10名青年,從黃河岸邊濟陽縣啟程,經過商河縣城由南向北走來。
他們從四面八方來到了同一個地方:樂陵——冀魯邊區抗日軍政學校。
冀魯邊區辦“抗大”
黑雲壓頂。風絲不透。
處暑裡“秋老虎”發威,熱得夜睡人躺在炕上翻燒餅。
午夜時分,樂陵城裡驀地竄出一彪人馬,他們偃旗息鼓,輕裝簡從,悄無聲息地疾步西行。似一陣風吹過,青紗帳發出沙沙聲響,夜貓子(貓頭鷹)止住叫聲,路邊野兔倉惶鑽進草叢,驚奇地看著這支隊伍呼呼走過。
后來在淮海戰役中負傷致殘的團政委劉文正清楚地記得:這一天,是1938年8月25日(處暑第二天)。當時他17歲。
這一天,劉文正和百余名八路軍戰士在永興支隊二營六連周保才(一為周志飛)連長帶領下,去執行一項重要的特殊任務:前往魯西夏津縣接應幾十名抗日軍政學校教官。
兩年前,不滿15歲的“小小鬼”劉文正在陝西參加了“鐵滾”——中國工農紅軍,當了紅二師政委肖華的勤務員。今年8月,肖華率領八路軍一一五師東進抗日挺進縱隊來到他的家鄉冀魯邊區。
抗日戰爭打響后,冀魯邊區遍地燃起抗日烽火,邊區民眾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紛紛拿起刀槍抗日殺敵。到1938年底,抗日武裝發展到1.5萬多人,鄉村黨支部、農救會、青救會、婦救會、兒童團紛紛建立。隨之存在的問題凸顯出來:部隊人員多數由農民、學生、教師組成,間雜三教九流人員,其成分復雜,思想復雜。戰士抗戰熱情高,但不會打仗,不懂戰術,干部不懂訓練和管理部隊,急需提高軍事和政治素質。再就是部隊嚴重缺乏干部,制約了戰斗力。因而,在挺進縱隊到來之前,第31支隊和先期到達冀魯邊區的永興支隊,已著手舉辦抗日干部培訓班、軍政訓練大隊。然而,因缺少教官,影響培訓質量。
肖華到達冀魯邊區根據地了解情況后,立即從縱隊直屬機關和永興支隊抽調部分干部充實到各部隊,同時確定仿效延安“抗大”,在縱隊司令部駐地樂陵興辦冀魯邊區抗日軍政學校,培養軍隊和地方工作干部。縱隊向一一五師代師長陳光、政委羅榮桓求援,派優秀干部來擔任教官。師部同意了請求,提出,這些干部身經百戰、文武兼備,是革命的寶貴財富,他們前來途中要通過敵人封鎖區和津浦路,必須確保他們的絕對安全。因此,必須派出部隊前往接應。肖華與參謀長鄧克明、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等同志反復研究,把這一任務交給了周保才連長。因為肖華的愛人王新蘭也在這次調配干部之中,劉文正受命參與了這次行動。
從樂陵前往夏津縣有兩條路,一條是南路經過德平(現為臨邑縣德平鎮)、陵縣、恩縣(現為平原縣恩城鎮),一條是西路經過寧津、吳橋、德縣(現為德州市德城區)、恩縣或武城縣。縱隊領導分析,南路近,但沿途黨組織和地方抗日武裝力量薄弱,民眾基礎差,一連人長途跋涉中一旦遭遇敵人,沒有接應,容易閃失。西路較遠,但沿途一半路程地帶是抗日根據地,相對安全。由此,選擇了走西路。
行前,肖華、符竹庭囑咐周保才:“這次任務特殊,沒有告訴沿途地方黨政組織和武裝,你們單獨行動,遇到敵人盡力避開,非打不可不要戀戰,絕對保証教官們安全。”周保才立正敬禮:“首長放心,一定完成任務!”
接近中午時分,周保才率隊行進到寧津縣西面王圃囤村附近,前方傳來幾聲槍響。偵察員氣喘吁吁跑來報告:“連長,有敵情!有一股‘小紅門’的紅槍隊在村頭路口跟偵察班接火了。”
當地“小紅門”人數眾多,組織的紅槍會投靠日偽軍,如果被他們糾纏住,會很快引來駐扎在寧津縣城和津浦路一帶的日偽軍,那樣情況就嚴重了。紅槍會不經打,但是今天打它不是時候。周保才當機立斷:“機槍班!”“有!”“你們靠近了紅槍會突然開火,打他個措手不及,全體戰士隨后跟進沖過去!”“是!”
“噠噠噠、噠噠噠”,槍聲爆響,突如其來,十數個紅槍會員倒下去,其他人隨即亂作一團,四處逃避。槍聲戛然而止,“嘩”地刮過一陣旋風。待驚魂未定的紅槍會員回過神來,周保才他們已無影無蹤。
越過津浦路,走出二三十裡,又遭遇馮二剝皮手下一股頑軍的阻擊。周保才考慮戰士們經過半夜半天強行軍已經疲憊,甩開敵人繞路而行,對這一帶地理情況不熟悉,若敵人尾追堵截,將造成被動。當下上策就是打退敵人,直沖過去。兩強相遇勇者勝。周保才指揮一排正面吸引、壓制敵人火力,命令二排、三排從兩側包抄過去,向敵人發起猛烈攻擊。經過一個多小時激戰,敵人潰退。
周保才帶領戰士趕到夏津八路軍駐地。師部首長了解了路上經歷,又增派一個連護送教官。9月2日早晨,戰士們身披霞光,迎著朝陽,興高採烈地高唱著《八路軍進行曲》大步走進樂陵城:“鐵流兩萬五千裡,直向著一個堅定的方向!苦斗十年鍛煉成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一旦強虜寇邊疆,慷慨悲歌奔戰場﹔首戰平型關,威名天下揚。游擊戰,敵后方,鏟除偽政權﹔游擊戰,敵后方,堅持反掃蕩﹔鋼刀插進敵胸膛。巍巍長白山,滔滔鴨綠江,誓復失地逐強梁。爭民族獨立,求人類解放,這神聖的重大責任,都擔在我們雙肩。”
隨后,冀魯邊區軍政訓練大隊改為抗日軍政學校開學了!由挺進縱隊政治部主任符竹庭任校長,曾慶紅任副校長,朱子偉任教育長,學制由1個月一期改為3個月一期。
我們是抗日者的先鋒
“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同學們,努力學習,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我們的作風﹔同學們,積極工作,艱苦奮斗,英勇犧牲,我們的傳統。像黃河之水,洶涌澎湃,把日寇驅逐於國土之東,向著新社會前進,前進,我們是抗日者的先鋒!”
嘹亮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從古城樂陵丁字街頭東側中學校園裡飄出,飛向廣袤的棗鄉原野。來自八路軍、地方抗日武裝、邊區黨政基層和友軍的戰士、愛國知識分子、熱血青年們,在軍校上午學習,早晨、下午軍訓,晚上討論。他們懷揣一個共同的目標: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學習艱苦而快樂。
馬沖(建國后曾任廣西農業廳林業處處長等職)對此記憶猶新:“當時沒有自己的政權,軍隊大部分時間打游擊,隨處籌糧食菜金,規定指戰員與學員同樣,每人每日小米一斤,青菜一斤,豬肉五錢,油鹽各三錢,每月每人津貼豬肉一斤或黃煙半斤的折價金,每年單衣兩套,棉衣一套,每月布鞋一雙,毛巾一條,兩月一雙襪子,一季一把牙刷牙粉,棉被一般三年一床,棉衣被換季時交公。”
“那時我們的學習條件非常困難,課本隻有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是鉛印本,也很難得到,其余如游擊戰術、馬國瑞同志的抗日民運原則、艾思奇同志的大眾哲學講話等,則全靠特委機關和部隊政治部用手刻蠟紙油印。刻印的小冊子,字小而密,卻非常精美清晰,本子小巧易藏。得到一本大家爭相傳抄,以讀為榮,當時求知若渴而得一識一息卻不易,所以讀后印象很深,討論也更認真。”
清晨,學員全副武裝在棗林裡排兵布陣。列隊、展開、臥倒、匍匐前進、瞄准、射擊、投彈、沖鋒、刺殺……“抗戰已發生,大炮響連聲,前方我弟兄,勇敢殺敵兵,拿一把青龍大刀顯威風,活活像關公。天色正黃昏,大炮剛剛停,前方我弟兄,沖殺鬼子兵,看他們一個一個臉發青,刀下送了命。男的上前線,婦女隨后跟,男的去打仗,婦女看傷兵,你看那男女老少齊上陣,痛殺鬼子兵。男女齊上陣,痛殺鬼子兵,殺聲喊連天,打敗日本鬼,你看那老頭小孩齊歡呼,勝利真光榮!一二三四!(《抗戰歌》)”
上午,操場上400多名學員列隊席地而坐,鴉雀無聲,聆聽肖華司令員作《放棄武漢后的形勢與當前的緊急任務》報告。肖華講到關鍵處揮動著手臂:“同志們,武漢失守后,日寇更向縱深擴展,敵軍戰線拉得越長,越力不能及,越有利於我軍開展敵后游擊戰。同時也要看到,日寇為了保住佔領區,下一步可能要以重兵回師掃蕩。目前我們的任務是,克服一切困難,堅定必勝信心,打垮日、偽、頑匪的四面圍攻,借打勝仗迅速地發展抗日武裝﹔大批培養軍政干部,提高戰斗力﹔宣傳黨的抗日救國政策,放手發動民眾,依靠民眾,逐級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發動一切抗日力量,堅持敵后游擊戰爭,爭取最后勝利。”
中午,毒辣的太陽晒爆了大地。一聲哨響,學員沖出宿舍奔向操場。教育長朱子偉已經風紀扣緊扣、身板筆直、立正站在烈日下。學員們知道,大雨滂沱、風卷飛雪天氣裡中午的哨聲,多數是朱子偉吹響的。朱子偉高聲說:“同志們,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它前一個名字叫紅軍,我們是勞苦大眾的隊伍,目標是解救全中國勞苦大眾。現在,日本鬼子強佔了我們的國土,眼看要亡國亡種,我們絕不當亡國奴!八路軍是抗日救國的先鋒隊,你們是先鋒隊的排頭兵。同志們要發揚紅軍爬雪山、過草地、吃草根、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夏練三伏,冬練三九,練身骨,練意志,練本領。練兵場上多流汗,到戰場上就少流血。”
李光遠終生難忘:“為了鍛練學員,一夜行軍五六十裡,次日又夜行軍八十余裡,連續兩夜的長途行軍,人困馬乏,不少人腳上磨起了泡,有些害怕吃苦的人開了小差。副校長曾慶紅、教育長朱子偉召開大會講話,勉勵學員堅定信心,克服困難,勇敢前進。同時公布願意回家者,允許回家。凡回家者,另列出一隊,隨即離開了隊伍。對多數留校的學員,進行了整頓。”
晚上,豆油燈下,學員們分組討論、交流學習體會。“小鬼子佔了大半個中國了,我原先發愁,啥時候才能把鬼子打出中國去呀。聽了符(竹庭)校長講毛主席《論持久戰》的三階段,我心裡算真亮堂了:持久戰跟兩個人撂跤一樣啊,開始咱身子骨弱,撂不過對方。隨著不斷長勁兒,兩人撂個平手了。接續著再長勁兒,就把對方撂倒了。”
“啥叫游擊戰?鄧(克明)參謀長講得好啊,游是走,擊是打,游而不擊是逃跑,擊而不游是拼命,這兩個辦法都不行。‘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進我退,敵退我追’,這16字訣把游擊戰術說到家了。”
“還有王(國華)主任講的兵民是勝利之本,咱們八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有老百姓支援咱們,瞧著吧,一定能打敗小鬼子。”
鑼鼓敲,琴弦奏,學員自編自演文藝節目,校園充滿了“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氣氛。文救會主任呂器創作的《難民參軍小調》搬上舞台:
左手拿著個瓢喲,懷中嬰兒抱,舉家逃荒,就把飯來要。
“你家住在哪裡?”
“家住在山東省,樂陵城正東,我的庄名叫‘高廷’。”
“老鄉,你為什麼來要飯?”
“同志們,你問那干甚麼?提起這事來很傷心,止不住兩眼淚紛紛。”
“去年的夏天,大水波浪翻,滿地的庄稼全被大水淹。”
“這水是誰放的呢?”
“問水是誰放,都是那小東洋,鬼子放水淹了地,使得遍地鬧災荒。”
“你們要飯,要到何處算一站呢?你們參加八路軍不好麼?”
“同志們的一席話,提醒我夢中人,咱們大家齊去參加八路軍。”
“參加八路軍,還不快走麼?”
“走、走、走,干、干、干,趕走日本鬼,大家得平安。”
文藝骨干燕明(建國后任上海市農委副主任、黨組成員等職)后來說:“那時候,學員還直接參加邊區的重大政治斗爭。”1938年10月,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來到樂陵,他對國民黨樂陵縣長牟宜之參加抗日活動極為不滿,沖著牟宜之大發雷霆,拍著桌子申斥牟宜之:“你是我的人,為什麼要聽共產黨指揮?!”牟宜之堅持立場,跳起來慷慨陳詞道:“我牟宜之長這麼大隻知道自己是中國人,誰堅持抗日、為民眾謀福利,我就聽誰指揮,把錢糧就送給誰,你就是把手指拍斷了也絲毫改變不了我的主張!”沈鴻烈惱羞成怒,以升遷為名要強行帶走牟宜之。
肖華對此早有預料,提前作了充分安排,組織萬人請願挽留抗日縣長牟宜之。燕明、石青等軍政學校學員按照司令部和邊區特委部署,圍住沈鴻烈的轎車,高呼口號:“擁護牟縣長主樂!”“挽留主張抗日的牟縣長!”“堅持抗戰,反對摩擦!”幾百名白發蒼蒼的老大爺、老大娘,跪倒在地,面對沈鴻烈衛兵架起的機槍毫不畏懼。眾怒難犯,沈鴻烈看難以帶走牟宜之,隻得狠狠地把他推下汽車。學員從中經受了鍛煉。
冀魯邊區的“抗大”,是培養軍政干部的搖籃。從1938年7月到1940年3月,前后共辦了7期,一期最短的1個月,最長的3個月,最多的一期學員1000多人,共培養了2000多名干部。這期間,邊區地方抗日武裝發展到2萬多人,黨員發展到2.5萬人。1940年3月,肖華所部八路軍主力分8批從冀魯邊區轉戰魯西、魯南地區,從這裡帶走了近2萬名子弟兵。
馳騁疆場殺敵寇
1938年初冬的一天,河北省東光縣縣大隊長王哲走出冀魯邊區抗日軍政學校大門,興奮地邊走邊唱起“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一堂?!”
眼下,王哲再唱《鬆花江上》這首歌,心情已由極度苦悶轉為斗志昂揚了。
1937年5月,因叛徒告密,哈爾濱黨組織遭受破壞,正在外地“讀書”的王哲接到“祖父病危速歸”的電報,躲避叛徒、日偽軍追捕,從黑龍江省來到河北省吳橋縣焦庄他姐夫家。王哲與黨組織失去聯系,如同天天生活在黑暗中,他記不清一天裡多少次悲憤地哼唱《鬆花江上》。不久,王哲幾經碾轉找到了中共津南特委負責人馬振華,接上了關系,投入發動民眾參加抗日的工作。1938年9月,王哲入冀魯邊區抗日軍政學校學習。
今天學習結業了,王哲按照組織派遣,到吳橋、德縣、德平三邊地區發展抗日武裝。這年冬天,王哲參與建立了德縣“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擔任大隊長。第二年9月,王哲同抗日軍政學校學員、德縣的武連鵬和德平縣的張龍組建了“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第二游擊大隊”,他任指導員。之后,王哲先后任德縣和東光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兼縣游擊大隊長。他率領游擊隊員在青紗帳裡打伏擊、交通要道上埋地雷、打炮樓、拔據點、炸軍火庫,出奇制勝,神出鬼沒,打得日偽軍寢食難安。
日偽軍打不垮王哲領導的游擊隊,便拉攏引誘,給王哲送來偽縣長的委任狀,被他當場撕得粉碎。敵人又派一名偽軍潛入游擊隊做內線,王哲識破后將計就計。一次,他故意把作戰行動方案透露出來,那個偽軍准時送出“情報”。第二天夜晚,日軍少佐中尾率大隊人馬前來“清剿”。王哲布下埋伏,敵人剛摸進埋伏圈踏響了地雷,游擊隊戰士們沖向敵人,槍聲、喊殺聲、手榴彈的爆炸聲響成一片。日偽軍遭到突然襲擊,亂作一團,慌忙迎戰。此戰打死打傷日偽軍300余人,繳獲敵人槍支500余件,子彈數千發,大獲全勝。日偽軍對王哲恨之入骨,貼出告示:“有斬八路王哲頭來獻者,賞大洋1000塊,生俘王哲來獻者,賞大洋2000塊。”
1943年4月27日,王哲和東光縣委書記李光前率領縣委、縣政府機關干部和戰士80余人,在河北省東光縣西大吳村被日本少佐中尾和大漢奸李文成(吳橋、東光等5縣“剿共”總司令)的近千名日偽軍包圍。王哲組織戰士奮勇突圍,剛剛殺出一條血路,又被沖上來的敵人堵死。敵人餓狼般地扑來,王哲和戰士們的子彈打光了……終因寡不敵眾,李光前、王哲等60多同志壯烈犧牲。王哲英年30歲。
1938年12月,馬沖在抗日軍政學校學習結業后,受冀魯邊區特委委派,回到臨邑縣組建了中共七縣(臨邑、商河、濟陽、齊河、禹城、陵縣、平原)工作委員會(簡稱“七縣”工委),他任工委書記。接著,白手起家組建抗日武裝。
“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經過周密計劃,1939年7月7日清早,由尚精貴、何風岐、劉來魁、蔡德禮等人,化裝成趕集的農民向臨邑城東門走去。走到城門前,正遇上一個偽軍開門上崗,幾個人突然沖上前去,捉住偽軍,用毛巾堵住嘴,捆綁起來。由蔡德禮看守,尚精貴同何風岐持槍飛快闖進偽軍宿舍,用槍口對准還在睡覺的偽軍,大喊一聲:“不許動!”劉來魁等人上前把挂在牆上的槍支摘下來,卸下槍栓捆在一起,命令偽軍起來穿衣服。就這樣,一槍未發,俘獲一個班的偽軍11人,繳獲長槍十支,彈藥一宗。
繼而,馬沖、尚精貴帶人接連消滅了偽軍一個班和一個排,他們從開始的十幾人很快發展到80多人。7月下旬,打出了“抗日環城大隊”大旗。后來,這支近400人的隊伍改編為八路軍魯北抗日支隊臨邑縣第一大隊。1940年春,在馬雲齊的帶領下,隨肖華司令員所率八路軍開往魯西戰場,成為威震敵膽的一支抗日武裝隊伍。
李光遠在抗日軍政學校學習結業,一路西行回到寧津縣。八年抗戰,他大部分時間在這塊土地上戰斗,真可謂是走刀刃,踩刀尖,步步驚險。回憶這段經歷,他感慨不已:“1941年夏天,我被任命為中共寧津縣長兼縣大隊長。寧津是日偽軍的治安‘模范縣’,駐有日偽軍2400多人,敵人在這裡實施了所謂‘治安肅正’、‘總力戰’、‘保甲制度’等統治手段,對村民實行十戶為甲、一村為保的保甲制,甲設甲長,保設保長。村村設情報員,村民都發良民証,實行連坐法。輔之以‘囚籠政策’,全縣821個村庄,設立了122個據點、崗樓﹔開挖了220多華裡深寬都是一丈五尺的洪溝,再用挖出的土在溝邊筑成一道高牆﹔修筑了46條總長475華裡的汽車公路。縣境內據點林立,洪溝縱橫,公路如網,把根據地切成條條塊塊,使抗日武裝主力無法展開,小股部隊都難以活動,企圖把抗日武裝扼殺在‘囚籠’中。”
極端殘酷嚇不倒八路軍英雄漢。李光遠領導縣大隊化整為零,分散活動,換下軍裝,隱蔽行動。
他們在我方掌控的村庄實行“二五減租”、分半減息、雇工增資、合理負擔,贏得民眾支持。
他們到近敵區村庄貼標語、散傳單、演出抗日節目,召集民眾開會:“鄉親們,黑暗是暫時的,隻要大家團結一心,就一定能夠打敗小鬼子。”
他們發動民眾開展打狗運動,便於抗日武裝夜間活動。
他們夜晚帶上刀槍和手榴彈,摸到日偽據點、崗樓前喊話:“偽軍弟兄們,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小鬼子在中國是兔子尾巴長不了,不要死心塌地給他們賣命!”
他們悄悄走進偽軍家裡做工作:“告訴你們的親人不要作惡,抗日政府和八路軍建有紅黑點功勞簿,誰作惡就在上面記個黑點,誰幫助八路軍就記個紅點。”
他們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現在罪大惡極的漢奸特務面前,殺一儆百,震懾敵人。
1944年8月1日,全縣軍民總動員,一夜即將敵人用一年時間修成的洪溝、多年來建成的公路干線和全部電話線,都進行了大破壞﹔將偽編鄉、保甲制、情報員完全解散取消了,戶口冊、“良民証”統統收起銷毀了,使敵人各個據點、崗樓都陷入了孤立癱瘓狀態。到這年初冬,寧津全境隻剩下5個據點,日偽的“模范縣”徹底垮台了。
……
歷經風雨滄桑,不變的是那段歷史事實。幾十年后,學員辛國治(建國后任南海艦隊副政委等職)、王猛(曾任武漢軍區副政委,國家體委主任、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等職)等將軍說起冀魯邊區抗日軍政學校飽含深情:“我們在那裡轉變了世界觀,由單純的抗日愛國思想轉變為共產主義思想,學到了軍事戰術。這些學員成為冀魯邊區黨政軍基層干部的中堅力量,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啊,抗日軍政學校,冀魯邊區抗日武裝的搖籃!(朱殿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