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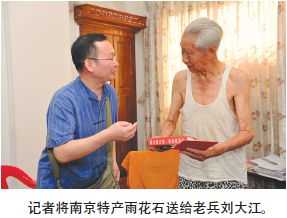

戴安瀾將軍塑像。

仁安羌大捷紀念碑。 滇緬公路上的中國遠征軍。
73年前,一個山花爛漫的春天,一支10萬人的中國軍隊,從雲南昆明金馬坊出發遠征異國,開始了一場艱難而悲壯的征戰。
70年前,也是一個春天,這支涅槃重生的軍隊,歷經九死一生的浴血反攻,終於擊敗了異族的入侵,捍衛了祖國的疆土。
這支軍隊,有個響亮而悲情的名字:中國遠征軍。
1942年到1945年,中國遠征軍赴緬作戰,以十萬將士埋骨他鄉的代價,打出讓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國軍威,將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聯為一體。其間,誕生於抗戰烽煙中的《新華日報》,以680篇的報道量,見証了這支軍隊血染沙場、馬革裹尸的全過程。
今天,讓我們翻開泛黃的舊報紙,踏著中國遠征軍的腳印,重溯70多年前的抗戰烽火,追訪“正義之勝”的精神與力量之源。
同古之戰
日軍驚呼“最強勁旅乃中國兵也”
中國軍隊為協助同盟軍作戰,已於日前奉令開入緬甸布防……
——1942年1月3日《新華日報》一版《我軍入緬協助同盟軍作戰》
2015年5月1日下午,記者來到中緬邊境雲南省龍陵縣境內的滇緬公路。並不寬闊的公路上車來車往,運輸繁忙。一塊“鬆山戰役舊址”的指示牌,顯示這附近曾經發生過戰役。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席卷東南亞,一直打到緬甸境內,矛頭直指滇緬公路。”中國遠征軍歷史研究專家戈叔亞說,當時國內90%以上戰略物資靠西方進口,而滇越線等其余運輸線均已被切斷,滇緬公路成為抗戰唯一的“生命線”。“如果滇緬公路也被切斷,中國就成了孤島,國內物資僅能維持三個月。”
這種情況下,中、英成立軍事同盟,商定共同守衛緬甸。於是,1942年初,車轔轔,馬蕭蕭,10萬遠征軍就從記者腳下的這條滇緬公路踏上了異國征程。這是甲午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派軍隊出國作戰。
翻開1942年的《新華日報》,濃重的“硝煙味”噴薄而出。同古戰役是遠征軍入緬后打的第一仗。由於英軍患得患失,致使遠征軍在邊境集結兩個月未能入緬,貽誤戰機。當1942年3月8日,遠征軍先頭部隊——抗戰名將戴安瀾率領的第5軍200師趕到同古時,日軍已於當天攻陷了仰光。
“盟軍計劃的同古會戰破產了。父親的任務是堅守同古一到兩周,牽制日軍北上。”戴安瀾之子戴澄東接受記者採訪時說,200師是孤軍深入,一無后援,二無重型武器,全靠血肉之軀對抗日軍的飛機大炮。
然而,孤守同古的戴安瀾給了不可一世的日軍最頑強的阻擊。2015年5月5日,記者在同古火車站看到,站台的柱子和鋼梁上,還密密麻麻地留有被槍炮打穿的彈孔,述說著當時戰斗之激烈。最終,200師死守同古12晝夜,直至彈盡糧絕,無奈撤出。
戈叔亞說,同古戰役雖敗,卻重創了日軍,殲敵5000余人,而200師自身傷亡不足2000人﹔同時為盟軍戰略部署贏得了時間。事后就連日軍東京指揮部也驚呼:自南進以來碰到的最強勁旅乃中國兵也!
仁安羌大捷
不計前嫌解救英軍7000人
由克安克巴邦出發之國軍克復油田中心之仁安羌,並救出被日軍包圍之英軍數千人。
——1942年4月21日《新華日報》二版《入緬國軍奏捷 仁安羌已經克復 救出被困英軍數千人》
2015年5月6日,記者頂著40多度的高溫,驅車6小時從同古趕赴仁安羌,“走進”那場震驚世界的戰役。
仁安羌郊外的501高地上,矗立著一座金光閃閃的佛塔狀紀念碑——仁安羌大捷紀念碑。該碑由仁安羌大捷的直接指揮者——遠征軍新38師113團團長劉放吾之子劉偉民發起建立。守碑的老僧告訴記者,當年中國軍和日軍就在此處爭奪陣地,打得血流成河。
“仁安羌大捷是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期間最漂亮的一仗!”戈叔亞說,同古失守后,中國戰區參謀長、遠征軍總指揮史迪威調集兵力,計劃實施曼德勒會戰,就在這時,西線仁安羌突然告急!
原來,在日軍的進攻下,防守西線的英軍連連潰敗。1942年4月17日,潰退中的英軍7000余人被日軍圍困在仁安羌。日軍迅速佔據仁安羌唯一水源——平牆河。高溫烈日加缺水,英軍近乎崩潰邊緣。
英軍司令亞歷山大緊急向遠征軍求援。遠征軍指揮部指令新38師師長孫立人派一個團去解救英軍。這項任務落到了113團團長劉放吾肩上。
家住同古的70歲華人楊文博告訴記者,他的父親楊伯方當年就是113團的汽車兵。“父親技術好,運送將士迅速而隱蔽,還受到了孫立人的表揚。” 楊文博說,“父親當時帶著一個排的汽車兵將113團將士星夜運達仁安羌。”
19日拂曉,僅有800人的113團向平牆河南岸的3000多日軍發起猛攻。據《新華日報》報道:“經二日之血戰,卒將仁安羌克復,並救出被多數日軍困圍之英軍,此役日軍死傷五百余,我軍僅死傷百余。”
戰斗中,113團3營營長張琦犧牲。“父親接到命令,將張琦營長的遺體運回后方。途中,因天氣炎熱,遺體開始腐爛,父親就在路旁流著淚將張營長遺體火化了。”楊文博說。
戈叔亞說,仁安羌一戰,中、英、美三國轟動。在遠征軍浴血掩護下,7000余英軍和500多傳教士及隨軍記者得以生還,從平牆河大橋上安全撤出。“更重要的是,這一仗打出了中國人的民族大義。同古戰役中,英軍突然單方面撤軍,將200師側翼暴露給日軍,直接導致了同古戰役失敗。而遠征軍不計前嫌,長途奔襲解救英軍,更彰顯出一種國際主義精神。”
攻克密支那
血戰80天肅清日寇
據東南亞盟軍總部宣布,密支那已被我軍攻克,城內日軍沒有一個活的……
——1944年8月5日《新華日報》二版《密支那攻克了》
2015年5月6日,記者來到密支那尋訪戰爭的痕跡。當地華人、遠征軍老兵后裔鄧恭標告訴記者,密支那原有三處遠征軍陣亡將士墓地,后因種種原因遭到破壞,現在這些遺跡全都不復存在了。
遠征軍的苦戰,未能挽回緬甸防御局勢的頹敗。二戰文物收藏家段生馗介紹,1942年5月,遠征軍開始撤退。
“一直跟蹤追擊遠征軍的日本56師團突然消失。十多天后,卻出現在遠征軍后方‘死穴’臘戍。”段生馗說,遠征軍后退路線被切斷,無奈,部隊在杜聿明帶領下,走上了一條“死亡之路”——數百公裡的叢林無人區野人山。
“正值雨季,山高林密,螞蟥蚊蚋成群,瘧疾流行,加上給養匱乏,部隊損失慘重。”段生馗說,8月初撤至印度和滇西時,十萬遠征軍僅剩四萬余人。200師師長戴安瀾在突圍中犧牲。
緬甸失守,日軍沿滇緬公路打入雲南滇西。中國失去了最后的陸上交通線,不得不重新開辟了代價昂貴而艱險的“駝峰航線”。
戈叔亞介紹,進入印度的遠征軍改編為“中國駐印軍”,1943年10月,發起緬北大反攻,先后攻克新平洋、於邦、孟關,突破胡康河谷、孟拱河谷,於1944年5月,兵臨緬北重鎮密支那城下。
“密支那戰役本是成功的奇襲空降戰,最后卻演變成慘烈的陣地戰。”段生馗說,美國指揮官的失誤,貽誤了戰機,使得日軍增援部隊趕到。
在密支那第二小學附近的一處高埂上,當地居民翁乃告訴記者,這裡就是雙方爭奪的陣地,“日軍佔據高地往下打,遠征軍自南朝北往上攻,到處是尸體。”
整整80天,中國駐印軍以傷亡6600多人的慘重代價,艱難收復密支那,日軍主力被殲滅。《新華日報》報道記述:“進攻密支那城南部和北部的我軍會師后,城內日軍全部被肅清。”
與此同時,駐守滇西的第二批中國遠征軍也發起了大反攻,強渡怒江,沿滇緬公路一路血戰,收復騰沖、龍陵、畹町等地,於1945年1月27日,與攻克八莫、南坎的中國駐印軍會師於芒友。至此,中印公路完全打通。隨后,駐印軍繼續揮師南下,於3月30日與英軍會師於喬梅。日軍全線退出緬甸。中國遠征軍使命全部完成。
戈叔亞表示,中國遠征軍異國征戰3年多,傷亡十余萬,“其最大意義,是粉碎了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戰略,阻擊了日軍的西進,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面勝利做出了貢獻。中國遠征軍用鮮血和生命,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歷史書寫了悲壯而輝煌的一頁。”
同期聲
戴澄東追憶父親戴安瀾將軍——
犧牲前,他深情地望著祖國的方向
“正義之勝”緬甸採訪組記者出發追訪之前,有幸聯系上了遠征軍抗日名將戴安瀾將軍之子戴澄東。
戴澄東現居南京,曾任江蘇省水利廳副廳長、江蘇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等職。1942年,戴安瀾在緬甸戰場犧牲時,戴澄東才1歲多。雖然沒有見過父親,但多年來,他一直在研究父親、研究中國遠征軍抗戰的歷史。
戴澄東告訴記者,戴安瀾率領的第5軍200師,是中國第一支摩托化部隊。1942年3月,200師作為中國遠征軍先頭部隊,率先入緬作戰。蔣介石親自趕到緬甸臘戍,為遠征軍壯行。
蔣介石單獨召見了戴安瀾,詢問第200師能否在同古堅守一兩周。戴安瀾當即表態:雖戰至一兵一卒,也要死守同古。
3月19日,同古大戰打響。“父親已做好殉國的准備,他寫了兩封遺書,一封給母親,一封給親友。”
戴安瀾寫給妻子王荷馨的遺書稱:“現在孤軍奮斗,決以全部犧牲以報國家養育,為國戰死,事極光榮……”
這封信的落款時間是“民國三十一年(即1942年)三月二十二日”,其時,同古城已被日軍的飛機大炮炸成一片廢墟。
而戴安瀾給三位親友寫的遺書,則意在托孤:“……余如戰死之后,妻子精神生活,已極痛苦,物質生活,更斷來源,望兄等為我善籌善后……”一位軍人、一位丈夫、一位父親的悲情與眷戀,躍然紙上,讀來讓人心酸不已。
戴澄東說,父親的遺書寫好后就放在了他的軍包裡。他犧牲后,軍包被送回家,母親看到遺書時,父親已犧牲一個多月了。
戴澄東告訴記者,父親的犧牲並非在同古戰役中,而是在緬北撤退時。同古戰役后,戴安瀾200師在杜聿明指揮下,打了一場漂亮的棠吉收復戰。然而,局部的勝利無法挽回整個戰局的失敗。隨著臘戍等地陷落,遠征軍奉令北撤回國。
“北撤途中,父親在突破敵人封鎖線時,被子彈打中腹部受傷。”戴澄東說。1942年5月26日,200師擺脫日軍追擊,抬著受傷的師長,來到緬北叢林深處一個叫茅邦的村寨。
據200師作戰日志記載,當天下午,戴安瀾精神突然好起來,讓部下扶起他,整理好衣冠,深情地朝著祖國的方向望了又望,然后壯烈犧牲,年僅38歲。這裡,距中國邊境僅有三四十裡。
“父親遺體被運回國內,國民政府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國葬。”戴澄東說。
記者手記
湮滅的遺跡, 不滅的意志
旅緬遠征軍老兵張富麟在世時,經常吟誦一首唐詩:“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騎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尤是金閨夢裡人。”這是中國遠征軍的寫照,也是這位老兵的悲壯心境。
行走緬甸,尋訪中國遠征軍戰場遺跡,我心裡也同樣升騰起另一種“悲壯”——被血火淬煉的歷史,激蕩著令人振奮的豪邁﹔而見証歷史的遺跡與記憶,卻在時光的風化中,漸漸湮滅。
“遺址永遠存在,遺跡都找不見了。”一位遠征軍老兵的后人這樣說。緬甸曾有十余處中國遠征軍陣亡將士墓地及紀念碑。由於歷史上的原因,這些墓地與紀念碑絕大多數都被破壞,僅有同古(又譯作東吁)一處紀念碑因處於緬甸國有學校內而得以幸存。在密支那,一位遠征軍老兵后裔帶我們尋訪了三處遠征軍墓地遺址——兩處變成了學校,一處成了居民區。如果不是有人帶著,你根本看不出這裡曾是殉國英雄們的埋骨之地。
老兵的血火記憶,也在隨著歲月的磨洗,漸漸遠去。散落在緬甸的遠征軍老兵,目前健在的還有15位,我們走訪了其中的5位。健在老兵中,年齡最大的已近百歲,最小的也超過90歲。處於風燭殘年的他們,許多人神智已不太清晰,記憶出現了混亂,無法准確回憶歷史。而他們的家人也已漸漸“緬化”——自小在緬甸長大,多數人不會講中文,對父輩的過往經歷隻知大概。記憶的傳承在這裡出現了斷層。隨著老兵們漸漸老去,這些最直觀的歷史記憶在一點點消逝。
然而,隨著尋訪的腳步漸漸深入,我們才體會到,鉤沉遠征軍歷史,不僅僅要記住他們的悲壯與輝煌,更要透過戰爭的烽煙,尋找一種不會被時光湮滅的永恆的東西。
終於,當我們走進歷史深處,在和老兵及后人們的對話中,在與學者專家的交流中,在對舊戰場遺址的尋訪中,在泛黃史籍的翻閱中,我們觸摸到了這種可以穿透歲月、可以永不磨滅的東西——意志。
在武器裝備遠遠落后於敵手的情況下,戰爭,打的就是意志。中國遠征軍由於給養差,出國征戰連雙軍鞋也沒有,穿著草鞋就上了戰場,因此被稱為“草鞋軍”。然而,就是這支草鞋軍,同古保衛戰中孤軍深入,在日軍飛機大炮狂轟濫炸下,在一片焦土與瓦礫的廢墟上,以血肉之軀阻擊日寇12晝夜,靠的就是頑強的意志。
打仗是一種意志,主動赴死又是一種意志。北撤途中,千余重傷員集體自盡,隻為不拖累大部隊的行軍﹔野人山裡,女兵拼盡最后的力氣跳下懸崖,隻為給生命留取最后一絲尊嚴。意志不只是勇氣,更是一腔奔涌的熱血和情懷。
赴死是一種意志,活著也是一種意志。大半個世紀的生涯中,旅緬老兵李光鈿堅持不入緬甸籍,以一種“純粹中國人”的身份,艱難生活在異域他鄉﹔人生的最后階段,老兵楊伯方守護著一塊遠征軍紀念碑,如同陪伴著昔日戰友,直至生命的盡頭。意志裡不僅有愛,更有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堅守。
軍人的意志,源於家國情懷,源於對祖國、民族無限的忠誠與摯愛。在這種意志的引領下,他們為疆土而戰,為尊嚴而戰,為獨立與自由而戰,雖浴血而無懼,雖百死而無悔。說到底,軍人的意志,更是一種民族精神。
策劃:周躍敏 劉守華 陳 鋼 統籌:彭廣余 視覺:沈 東 供圖:新華報業視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