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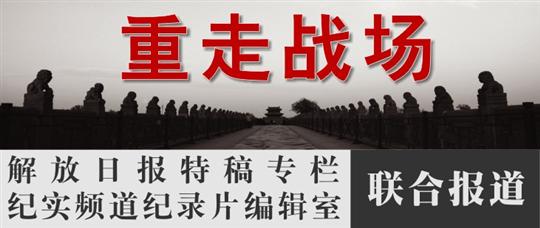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寸草不長的卵石地上,曹景行聽到一位小孩問奶奶:地上怎麼有這麼多灰色的小石子?奶奶回答:每一顆石子,都是一條人命。
南京是上海廣播電視台紀實頻道《紀錄片編輯室》“行走戰場”攝制組近日攜手曹景行重訪戰場的首站。“卅萬亡靈,飲恨江城。日月慘淡,寰宇震驚。獸行暴虐,曠世未聞。同胞何辜,國難正殷。”正如紀念館內公祭鼎上鐫刻的銘文,日軍在華所煉的血淋淋地獄,不忍卒睹。
家國痛,山河哭。一位1938年春夏在中國周歷的英國記者,親眼見証日軍暴行后說:“中國民眾由於慘痛的經歷,開始明白自己的命運。體格強健的平民,幾乎每一位都加入了游擊隊。我每天聽到他們語言中表露著對侵略者的痛恨。他們為國土而戰斗的決心,非常顯著。”另一位英國記者當年也說:“一切日本的計劃,顯然忽略了一點:中國民眾的長期抵抗。”
同仇敵愾,共御外敵。千千萬萬中國軍民的抗戰,創出了世界戰史上極為罕見的正面、敵后“雙戰場”奇觀。
曹景行之父、首位發布台兒庄大捷新聞的戰地記者曹聚仁,在其1947年參與編著出版的《中國抗戰畫史》裡,將這第一部內容完備的中國抗戰史,定義為非崇功頌聖的、“人民的戰史”。
抗戰勝利70年后的今天,“曹景行們”每一處“行走戰場”,都是一次關於我們、對歷史的現實叩問——
我們紀念什麼?我們守護什麼?我們捍衛什麼?
苦難
老曹行走戰場23日是我們南京拍攝最后一天,上午到中山門城頭,南師大經盛鴻教授講述78年前的南京保衛戰。一位手提菜袋的老漢經過時看了我們一眼,憑直覺我請他留步,一問果然是經歷整個日佔時期的本地居民,今年84歲,日本人打來時6歲。他滔滔不絕講述那8年經歷與所見,屠殺、毀家、逃命、苟生、屈辱。
——摘自資深新聞評論員、鳳凰衛視資訊台前副台長曹景行的微博
曹景行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隨訪時,不願稱對方為“游客”,而稱作“參觀者”。
當累累白骨近在眼前、痛擊心底,誰還會去介懷老曹這一點文字上較真的悼意。
“5號遺骸是名6歲兒童,頭顱在胸肋處,可証實掩埋之前頭頸已分離……”年輕的講解員顏雪姣向曹景行介紹“萬人坑”遺址:坑內是經嚴格鑒定被確認為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遺骨,目前經考古發掘出表層208具,男女老幼都有,年齡最小者僅3歲,“下層還有很多未挖”。
78年前,在長達6周的南京大屠殺慘案中,平均每隔12秒,就有一位無辜中國人喪生!
慘案發生10年后,曹聚仁和戰地記者、攝影記者舒宗僑出版了《中國抗戰畫史》,用20余萬文字、數千張珍貴照片記錄了大量日軍侵華罪証和中國人抗戰事跡,堪稱第一部內容完備、見解獨到的中國抗戰史著。
曹景行說,父親告訴他,《中國抗戰畫史》裡一些南京大屠殺的照片,是當年父親採訪葉挺時,葉挺將其從日本軍官公文包裡繳獲的照片贈予。書中還載有《紐約時報》記者竇爾登、英國《曼徹斯特導報》記者田伯烈等人所記的“日人獸行”,“父親將自己當作一個百年后的史人來審訂史料,力求公正、真實,要對得起戰場上的將士,更要對得起下一代讀者,絕不歪曲事實”。
1948年8月,上海乍浦路軍事法庭審訊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茨,法官石美瑜的審判台上,就放著這本厚重的《中國抗戰畫史》。
見証比比皆是。5月23日,曹景行與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經盛鴻在中山門城頭,隨機採訪的老漢,開口就是親歷的苦難。老人姓趙,是土生土長的南京人,家被炮火炸得一塌糊涂,曾親眼目睹一個塘裡全是尸體。飢餓難當時,他就從剩飯剩菜的垃圾裡頭淘點吃的。
站在城牆上,曹景行與經盛鴻注視著手裡一張照片,那是78年前12月17日侵華日軍舉行的攻佔南京入城式。日本軍官騎著馬,耀武揚威,入的正是中山門。
鐵蹄踏入中國,戰火連綿,生靈涂炭,餓殍遍野。而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是二戰史上“三大慘案”之一﹔另兩大慘案,除了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就是奧斯維辛集中營慘案——那些用人脂造出的肥皂,用毛發編織的地毯,那種把人一堆堆趕進毒氣室裡的“洗澡”,同樣是人類文明史上至為黑暗的一頁!
中國和世界共此悲慟。“任何人要否認南京大屠殺慘案這一事實,歷史不會答應,30萬無辜死難者的亡靈不會答應,13億中國人民不會答應,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與正義的人民都不會答應。”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講話,擲地有聲。
在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多幅既似書法又似繪畫的條幅懸挂空中。館長吳先斌說,它們都出自日本的反戰畫家。
其中一張條幅,上書四字“南京慟哭”,大字鮮紅,筆畫斷斷續續,仿佛帶血的眼淚流下來。
抗爭
“青春,奔騰在大江。熱血,綿延在高山。聲聲號角,萬眾戎衣,這是保衛母親的意志。”這是我為這次重訪寫的主題曲《山河行》的部分。為了保衛母親,為了保衛原本小橋流水、有樹有花的寧靜生活,那麼多風華正茂的中國人英勇從軍、不畏犧牲。很多人的出發點,其實十分朴素,一個詞可概之:和平。
——據《紀錄片編輯室》總制片人黃瀛灝
還我河山!已故美國知名記者約翰·甘瑟曾說:“這一場戰爭,反令中國成為一個空前團結和堅強的戰斗單位。”
1937年12月16日,南京已陷落,蔣介石發表告國民書。據《中國抗戰畫史》,其中宣告了抗戰到底的決心:“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后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在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當徹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后勝利之信心。”
就在《中國抗戰畫史》的同一頁,寫道:“同月25日,共產黨也發表對時局宣言”——“我們抗戰目前正處在一個嚴重的困難關頭,然而部分領土和中心城市的損失,初期戰線上的部分軍事的成敗,均不能決定中日戰爭的最后命運﹔而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堅強團結和長期艱苦抗戰之毅力與信心,實為爭取最后勝利之保証。”
一如“七七事變”后紅軍高級將領致電國民政府表示“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命為抗日前鋒,與日寇決一死戰”的錚錚誓言。8年浴血奮戰,中國人民傷亡3500萬,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重大貢獻。
1937年8月,淞滬會戰。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步平稱,這是“中日雙方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第一場大型會戰,標志全面戰爭的真正開始”。
一個多月后,忻口戰役。中國第二戰區司令部將戰區部隊編為右翼軍、中央軍、左翼軍和總預備隊,分別歸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國民黨將領衛立煌、楊愛源、傅作義指揮。而朱德統領的右翼軍除八路軍以外,還包括國民黨軍隊。曹景行說,那是他的叔叔曹藝,血戰過的地方。
1937年11月,日軍兵分三路圍攻南京,國民政府倉促布置南京保衛戰,並宣布遷都重慶。經盛鴻看過一張當年城牆上作戰的照片,“中國守軍用步槍、手榴彈、炸藥包拼死戰斗,而敵人早已進入飛機、大炮的熱兵器時代,再厚的城牆也不堪一擊……”
1938年初,日軍為打通津浦鐵路建立起南北戰場的聯系,4萬人進攻徐州門戶台兒庄。台兒庄大捷,即戰地記者曹聚仁第一個向世界發布的,是中國軍隊抗日戰爭開始后的最大勝利。
1938年6月,日軍集結35萬兵力及海軍艦艇、軍機,進犯水陸交通樞紐武漢。會戰持續4個半月,日軍“速戰速決”佔領中國的計劃嚴重受挫。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中國守住半壁河山﹔1939年9月,二戰在歐洲爆發,中國的敵后戰場逐漸成為抗日戰爭主戰場……
在位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歷經30多年尋找、整理出的近20萬抗日陣亡將士名錄數據庫,近日上線。工作人員告知,今年來查的人是往年的好幾倍,然而查到的比例極小。畢竟,名錄目前僅近20萬之數,只是滄海一粟。
5月22日下午,四川男子張穎,在電腦的數據庫查找外公高維華的名字﹔74歲的南京人石女士,在問訊處向工作人員查找她父親的名字。
高維華,年輕的營長,29歲時在淞滬會戰中陣亡。那一年,張穎的母親僅1歲。張穎的外婆守寡多年,郁郁早逝。如今,外公19歲的戎裝英姿,存在張穎的手機裡。
石女士的父親,軍需主任,1943年抗戰中犧牲。那一年,她2歲多。她所知的父親訊息甚少,后來有人告訴她,父親是國民黨裡的中共地下黨員,卻無法確証。
最終,張穎查到了。這位50多歲的漢子,緊緊握住了身邊曹景行的手,哽咽。
石女士沒有查到。她沉默了一會兒,喃喃道,或許海峽對岸找得到。
捍衛
民間的力量,在這次特別的旅程中讓我們“85后”尤為震撼。前人的兀立不屈,今人的尋訪紀念,都在一遍遍觸動心靈。我們的拍攝,是向歷史致敬,也是在向這些平凡又偉大的中國人致敬。
——據《紀錄片編輯室》“行走戰場”南京站的編導左上
吳先斌剛從北京潘家園購得一套“寶貝”——上海的 《良友》畫報在淞滬會戰時期的抗戰特刊,花了4萬元。
這位時常頭戴紅五星帽子的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館長,每年自費投入兩三百萬元。
他是老兵后代?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后代?都不是。他原是裝飾廠的老板,現在開了小額貸款公司,博物館樓下也出租了,為了供養這個不折不扣的民間博物館。
那是為何?隻因他曾在地攤上覓得一本日本部隊佔領南京的影集,驚覺自己全然不熟悉這段歷史,從此開始收集資料、走訪抗戰老兵。
“我就是希望越來越多人了解、關注這段歷史。”開館9年,博物館已接待參觀者十幾萬人次,包括日本、德國、中國台灣的民間團體。最近,吳先斌正在掃描館內所有資料、擴容網站,以供更多人知曉。
經盛鴻教授的尋訪,就更有年頭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他開始收集鮮為人知的歷史資料,並耗時十多年查找到40多個慰安所遺址。2003年廣受關注的朝鮮“慰安婦”朴永心回南京指認慰安所遺址,正是源於經盛鴻與日本學者的共同努力。
一切,都是為了歷史不被掩埋。
今年4月,“中國遠征軍緬甸陣亡將士遺骸尋找與歸葬項目”在緬甸密支那中國遠征軍新一軍墓地遺址正式啟動,接老兵遺骸回家,安息。
今年6月,東北地區首家保護研究展示抗戰遺跡的區域性民間組織——東北抗戰遺跡聯盟成立。在這些抗戰遺跡中,就有楊靖宇的戰斗足跡,那位犧牲時腸胃裡隻有棉絮和草根的東北抗聯第一路軍總司令。
去年盧溝橋畔的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七十七周年儀式上,習近平總書記與兩位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兵,以及兩名少年兒童,一同為雕塑揭幕。一位老兵是新四軍老戰士,另一位是國民黨老戰士。
尋訪、研究、紀念,正是為了守護真相,為了捍衛和平。“歷史告訴我們,和平是需要爭取的,和平是需要維護的。”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講解員顏雪姣,學的是二胡演奏專業。她每周六都要與同事們參加音樂會。實際上,館內有十來位講解員均從藝術院校畢業。演奏舞台就在館內,名為“和平大舞台”。
“我們所寫的雖是關於戰爭的記錄,但希望由此而閃出促成世界和平的光輝。”這句話引自《中國抗戰畫史》的扉語。
1945年9月,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陸軍總司令部舉行。
南京!南京!銘記歷史,捍衛和平。(記者 林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