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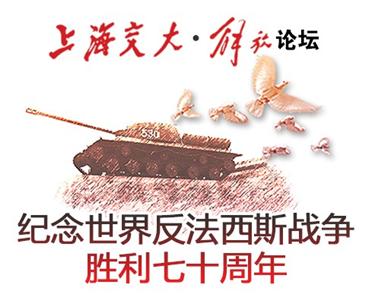
無圖說
復旦大學教授、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 沈丁立
70年前的8月6日和8月9日,日本廣島與長崎分別遭受原子彈轟炸。這一被稱為“原爆”的空前攻擊在瞬間摧毀了這兩座城市,並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給當時的日本政府與社會以巨大的心理壓力,從而在客觀上加速了以日本投降為標志的二戰結束。
世界上首次原子彈爆炸發生在美國,是1945年7月16日美國政府在新墨西哥州阿拉默戈多沙漠上空投擲的用以考察原爆效應的實體試驗,此后美國在日本投放的兩枚原子彈則是首次用以實戰。當時,面對聞所未聞的攻擊,日本政府深感驚愕,對美國能以一個炸彈在極短時間內毀滅一座城市的戰爭能力極感震撼。面對美國手上還有幾枚核彈從而能夠繼續摧毀其他日本城市的前景,日本被迫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投降要求。
二戰結束已經70年,日本已從昔日戰敗國的廢墟上重新崛起,並走過一段和平道路。但它未來如何前行,二戰結束以后日本的心路歷程如何,兩次針對日本實施的核子攻擊又對日本產生了何種復雜后果,世人都在探究。
萌發“受害感”
美國總統杜魯門將上述核爆稱作“上帝對日本的懲罰”。確實,核裂變產生的巨大能量在瞬間奪去了廣島和長崎各約十萬人的生命,均為當時這兩座城市全部人員的大約一半。原爆所釋放的大量熱能、光能、動能以及放射能對爆炸中心附近的人員生命與財產造成的威脅是無與倫比的。不僅這種攻擊即時造成巨大破壞,它對幸存人員與環境所造成的長期破壞更是難以估量。
對於美國以核武器攻擊日本所產生的法律和道德辯論,從來就不曾消停。盡管人類迄今未能禁絕戰爭,但國際社會已發展了包括在戰爭期間限制攻擊民用目標的倫理與法則。美國在核打擊日本前已事先做過核武器效應試驗,能判斷對城市進行核打擊將產生的嚴重后果,但它仍決策實施攻擊,其目的就是要利用這種效應所產生的威懾,因此也不免引起爭議。
美國的自辯則是這兩座城市本身高度軍事化,在日本拒降情況下以常規武力逐城逐巷對日本本土實施常規攻擊,將給美軍帶來巨大傷亡,並可能給日本在整體上帶來更大破壞。但是這種說法未能充分說服日本。美國為紀念二戰結束50周年,於1994年發行“蘑菇雲郵票”,但因面臨日方的強烈不滿而在郵票發行后又予以取消。
對當今世界而言,70年前的這場核攻擊影響重大。首先,在一些人看來,核武器無區分殺傷的特性使其帶上了背離人道甚至和平的標簽,從而防止核武器等大規模毀傷性武器的擴散成了當代國際安全的主要議題,全面禁止與徹底銷毀核武器的理想主義主張也不時粉墨登場。其次,正由於核武器的巨大毀傷作用,包括它能促使武裝到牙齒的日本帝國投降的能力,這種武器也就成了大國博弈的實力基礎,過去幾十年來各國尋求核武器的故事已在世界各地屢屢上演。
但70年來,日本在長期強調自己是原爆受害者的同時,集體回避了造成這一攻擊的前因后果。應該說,美國對日本實施原子攻擊的國際政治后果極為復雜,但這並不能給日本政府以及民眾罔顧本國因對外侵略而給他國帶來巨大損害的事實以任何理由。必須指出,受害者對侵略者以報復是公平的,至於如何以符合戰爭倫理所要求的對稱性與比例性實施報復,則可進行學術探討。然而,二戰結束以來無論是廣島、長崎還是日本中央政府,或者是日本精英以及一般民眾,都過度強調了日本是原爆受害者,從而在當代日本的國家敘事中,加害者的事實被忽視,加害者儼然成了受害者。
產生“厭核感”
日本是迄今唯一受過核打擊的國家,因此日本民眾的心靈普遍存在悲情。所以對於是否發展核武器,在日本大抵是個議題禁區。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在二戰后曾經長期存在過的泛和平主義要求本國遠離核武器。譬如,日本民眾普遍認為作為經受過核打擊的國家,不發展核武器乃天經地義。為此,日本以非核武器國家身份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它還曾經發布“無核三原則”,即“不制造,不擁有,不運進”核武器。
但是,日本戰后的核認知在政府和民間存在相當差異。盡管日本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但是日本政府對此曾經躊躇不前。在正式加入前,日本政府內部的秘密部際備忘錄曾表示即使日本不制造核武器,但還是應該具有制造核武器每個部件的能力。近年揭露出來的新的事實表明,即使日本政府曾經信誓旦旦地表示不運進核武器,但當年的自民黨政府還是與美方達成核密約,以書面方式向美國承諾對進入日本的美國艦艇是否攜帶核武器不予追究。從這些情況下,日本普通民眾厭核是一回事,但日本政府在核武器問題上出爾反爾,對美國駐軍核武器保持曖昧則是另一回事。作為美國的東亞盟國,日本享有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美國為日本撐起了核威懾的保護傘,東京的核政策也就很難真正獨立。
雖然日本在名義上是非核武器國家,但日本受到核武器國家的延伸威懾保護,就已經削弱了日本的非核武器國家的信譽。更有甚者,日本在發展民用核能的名義下,已大量囤積裂變材料。雖然這些材料尚未達到核武器級,但隻要對其繼續提純,目前日本已經積累的核材料就可制造數千枚在廣島與長崎使用過的核彈。所以,日本的准核武器能力已經十分可觀。
扮演“道義感”
日本因受原爆攻擊而曾面臨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這一因素已成功為日本所用,儼然成為日本的“軟實力”,日方在國際政治舞台也屢屢就此打出“道德”核牌。日本的做法有三:號召全球核裁軍﹔批評中國強化核威懾﹔借二戰結束70年之際,呼吁各國領導人在今年訪問廣島與長崎。
長期以來,日本在國際社會核軍控與核裁軍問題上扮演著活躍角色,其中不乏經過精心算計的“內涵”。日本主張全球核裁軍,但落腳點往往就在東北亞。這個地區的日本和韓國都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非核武器成員,所以日本的政治議程實際上就是對中國和朝鮮施加壓力。然而,日本對自己的角色則往往是輕描淡寫,絕口不提日本之所以還是非核武器國家,其背景是美國提供了核保護,因此它間接享有了核威懾,而一旦同盟出現風險,日本未必還能堅守無核原則。
盡管二戰已結束70年,但在日本的地緣戰略考量上,中國仍是其核心競爭對象。盯緊當代中國核戰略、核力量的發展,是日本戰略界的頭等大事。近年來,日方對我國的核力量現代化十分關注。日本一方面踏上了美國“亞太再平衡”的戰車,緊密呼應美國在東亞制衡我國的戰略部署,另一方面在國際社會塑造中國核擴軍的形象,其心機不可謂不深重。
在今年聯合國舉行的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五年一度的審議大會上,日本試圖在最終文件中納入呼吁各國領導人前往廣島與長崎訪問的內容,在本質上仍將自己裝扮成受害者而回避其本身更是加害者的事實。日本的做法引起中國等國家的不滿,中方對此進行了抵制,並向各國作出說明。中國同情廣島和長崎人民蒙受原爆攻擊所帶來的苦難,但認為蒙受苦難的不僅僅是日本人,更多的還是經受了日本對外侵略所帶來災難的東亞與亞太地區的各國人民。日本不應漠視其昔日對他國人民造成的傷害,不應在二戰70年后仍對自己罪惡的過去熟視無睹。
70年來,日本在核問題上呈現的“三感”,無疑令人感到日本在歷史和現實的認知上都存在誤區。出於各種原因,日本確實走了70年的和平道路,但對它未來何去何從,人們有著擔心。這不是由於日本沒有理由為廣島和長崎原爆產生悲情,而是因為日本對事物因果缺乏反省精神與能力。
這樣的日本,做什麼都會打折扣。由於缺少勇氣,日本難以站得更高,這也同樣是其理想與現實之差距的根本原因。日本當局欲利用戰后70周年之際,推動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獲得更高關注。但是,由於東京變本加厲奉行歷史修正主義,70周年之時反而成為國際社會對日本“右轉”進行全面檢視的良機,日本和平主義還能堅持多久已被打上偌大問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