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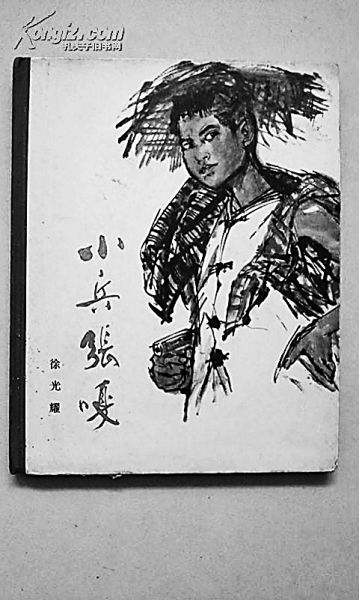
他的作品像他的名字一樣,在群星閃耀的文壇熠熠生輝﹔他塑造的“小兵張嘎”在中國文學史數不勝數的人物群像中無可替代。
他就是徐光耀。
一個13歲參加八路軍,親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各個歷史時期的九旬作家。他創作的長篇小說《平原烈火》和中篇小說《小兵張嘎》迄今風行不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者,他2000年出版的《昨夜西風凋碧樹》獲得了第二屆魯迅文學獎。
如今,徐光耀千萬字日記陸續出版。這裡有生活的原色,更是時代的切片。
作家聞章是徐光耀日記整理者之一。他說,徐光耀的日記所呈現的原生態的、活生生的內容,可以拍無數電視劇。他的日記把自己的弱點,包括固執狹隘等等全部暴露。但是,聞章說:“這是他超越個人的無私奉獻。他在我眼裡的形象更高大了。”
戰 斗
徐光耀是在抗日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作家。
1942年“五一大掃蕩”的時候,徐光耀正在冀中一支縣游擊隊裡工作,活動在石德路南的寧晉一帶。那時環境的殘酷自不待說,敵我兩方的每一舉動,不僅與游擊隊活動的成敗相關,也直接與個人的生死相關。
敵人用點線織成了網,哪一據點增加了兵力,都立刻構成對你的直接威脅。戰斗很頻繁,過幾天總要打一仗,有時一天打三仗,還常常被敵人四面八方包圍起來。隻要有戰斗,上至大隊長,下至炊事員,不管你有槍無槍,都得參加沖鋒或是突圍。
徐光耀那時18歲,家信還寫不大通,當然沒有想到這些都是小說“材料”,但那時所見的每一種現象、每一個人物,那一腳一步、一舉一動,卻都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記得有時在地洞裡,大家閑談,常常會說:“抗戰勝利以后,再想想今天的斗爭,不定多麼有意思哩!”有時也偶爾想到如果有人把這些編成書,實在太好了,也太應該了。然而,這在當時僅是一種渺茫而遙遠的希望,偶爾一閃罷了。
抗戰勝利以后,1946年,冀中發起過一個“抗戰八年寫作運動”,號召每一個識字的人,都來寫寫自己在八年抗戰中最令人感動的事跡。
徐光耀為這運動所鼓舞,也寫了兩篇類似報告的東西。其中一篇是《斗爭中成長壯大》,寫一支游擊隊在“大掃蕩”中,如何由失敗、退卻經過整頓和斗爭又成長起來走向勝利。他開始寫時就毫無信心,寫成發出去后,也就沒了消息。
1947年,徐光耀得到機會到華北聯大文學系去學習了八個月。這一次學習對他來說很有意義,就在那時候他才稍稍知道些所謂的“創作”,才知道文學作品中的形象應該主要是人物,獲得了一些文學上的基礎知識。也是在那個時候,他才模模糊糊覺得:表現“五一大掃蕩”那段斗爭的責任,自己也應該擔負一下,不一定非指望別人。
1948年,徐光耀又回到了部隊,隨后參加了綏遠戰役、平津張戰役、太原戰役,全國展開勝利大進軍,華北也全部解放。形勢給徐光耀帶來更大的鼓舞,新涌現的戰斗英雄的故事也不斷傳來。這時候,他情緒上、認識上忽然有個變化,給思路打開了一道缺口。
徐光耀開始不斷反思:為什麼在自己過去的作品中,從來沒有解答過“解放軍為什麼打勝仗?為什麼能在殘酷環境中由小到大並完全戰勝了優勢的敵人?”等問題,他開始嘗試解決為什麼隻看見“落后”面,看不見光明面,隻懂得寫轉變,不懂得寫英雄的問題。這一要求,對徐光耀將來的寫作有著重大的影響。
1950年,徐光耀用了40天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平原烈火》。作品一炮打響,他把成功的經驗概括為——
“第一,生活有積累,八年抗戰我在一線﹔第二,有基礎,我編故事的能力比較強﹔第三,抗日材料很豐富。《平原烈火》裡70%是真人真事,30%是虛構,用文學語言比較好表現出來,所以寫得比較快,不用多大力氣加工。”
恩 人
1955年批“丁陳反黨小集團”,徐光耀收到了一封以中國作協名義發來的絕密字樣的調查丁玲等人的外調函。信中提了六個問題,包括丁玲在文研所是否搞個人崇拜,是否搞過一本書主義等。
徐光耀寫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說:“我希望作協黨組能汲取這樣的教訓,在開展思想斗爭的時候,盡量避免使用壓力,防止造成那麼一種空氣,即沒有人敢講反對意見。”似乎意猶未盡,他在信的末尾又強調:“我對你們這次給我的來信,有一種在態度上不夠全面和不夠客觀的感覺,隻問我受了一本書主義的什麼影響,卻沒有要我對這些問題的反証,也沒有問我受過她什麼好的影響。這使我有些擔心,這樣的調查會不會得到完全公平的結果。”
因為這封信所述的事實,為丁玲翻案有利,1957年“反右”時,成為徐光耀“為丁玲翻案”的罪名,他被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在評論家雷達看來,徐光耀的可貴就在於,他不自私,不巧滑,不世故,不知利劍已懸在頭頂,“傻乎乎地”堅持著實事求是的精神。
在批斗了三四個月之后,他們讓徐光耀閉門思過,不給任何任務,實際上也沒有任何人理他。
這時,徐光耀自己在屋子裡進行苦悶的思想斗爭。他想,自己在黨的部隊裡長大,在黨的部隊裡成人,忽然成了右派,這使他的神經有點錯亂,見了自己的孩子,都覺得他是討債鬼。“我懷疑自己瘋了,我嚇壞了,我覺得瘋了還不如死掉。我想,得有個法子來救自己。”
當時找不出什麼法子。徐光耀看了一大堆書,看了12本莎士比亞戲劇集,看完合上書本想總結一下有什麼收獲,但是一條也想不起來。他想劇本的具體情節,仍然是一片空白。
不能讀書,不能出門,不能看戲,沒有出路。怎麼救自己?這時他忽然想起自己看過一本蘇聯版的心理學書,說人在遇到巨大挫折時,如果不好好控制,會走上危險的道路,有可能產生精神分裂。有什麼法子治?書裡提了八個字徐光耀記住了:集中精力,轉移方向。
不想自己受冤枉的事情,最有效的法子是創作。徐光耀的《平原烈火》裡面有個小人物,開頭挺活躍,后來沒有機會表現他,作品就結束了。這是他的遺憾。這個人物成為后來的“嘎子”。
“我對自己的個性不滿意,比較呆板,不活潑,我不喜歡這種性格,我喜歡的性格就是嘎子的性格,於是我回想這輩子碰到的哪些嘎子,想一條就在桌子上記一條,嘎人嘎事記了很長的單子,哪些是幼稚的,哪些是進步的,哪些是成熟的,把嘎子放在戰爭環境中進行排列調整,嘎子的形象在我腦子裡活蹦亂跳,后來寫成了《小兵張嘎》。”
徐光耀說,《小兵張嘎》是救命恩人,拉著自己投入創作,他全身心地寫嘎子,把自己受冤枉挨整的事情全忘了,身體也恢復得很快。
《小兵張嘎》是徐光耀用生命塑造出來的,出版快60年了,差不多每年都在印一兩本,“文革”時期也沒有中斷過。進入新時期以來,又被編入《戰斗的童年文學叢書》和《小學生叢書》,是被時光檢驗過的“紅色經典”。
寫這部作品,徐光耀得出的結論是,無論寫小說還是寫戲劇,無論中短篇還是長篇創作,最重要的是人物。中國的文學史非常有力地証明了這一點,《紅樓夢》《西游記》《水滸》,真正的經典作品就是非常典型的人物,我們可以忘記故事,但是忘不了人物,那些人物在現實生活中和我們一起成長。
徐光耀說,自己一輩子要寫出5000字像《紅樓夢》一樣的作品,就滿足了。
情 結
回顧一生,徐光耀有兩件大事刻在心靈上的烙印最深,給自己的生活、思想、行動的影響也最大,成為他一生中的兩大“情結”。這便是:抗日戰爭和“反右派運動”。
抗日情結使徐光耀的小說絕大部分是寫抗日的,4部電影裡有3部寫抗日。他說,如果沒有抗戰經歷,沒有那麼多經歷,自己不可能寫出那麼多作品,這段經歷使他除了抗日也寫不出別的,離開抗日他幾乎沒有作品。
“反右派運動”之所以成為他的另一“情結”,是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徐光耀中年以后的命運——
“它把我的心劈開了,撕掉了我的眼罩,使我看見了先前不曾看到的東西,盡管很難相信,卻眼花繚亂,迷迷糊糊。等到‘文化大革命’來了,又幾經天旋地轉,才慢慢有點兒明白,於是忐忑地間隔地寫了幾篇文章,這便是已收進這個集子的《我的喜劇》系列。”
徐光耀直到過了七十歲,已入沉沉暮年,時常聽到人們對“陽謀”現象的研議,才又有些新的感悟,《昨夜西風凋碧樹》由此形成。
《昨夜西風凋碧樹》是徐光耀的收官之作,是他用全部生命力量寫成的作品。
徐光耀並不是平反之后馬上寫《昨夜西風凋碧樹》,而是想了很多年。看過這本書的讀者一般的反應是,徐光耀是受了委屈,但是寫得平靜,沒有發火。
時任河北省作協主席的鐵凝認為,《昨夜西風凋碧樹》是在徐光耀生命的泥土中長成的綠樹,是他對生活的真實記憶和深入思考的結晶。在這部作品中,他深刻地反思了我們曾經走過的一段“頭朝下、腳朝上的歷史”,做到了魯迅先生所說的: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鮮血。重要的是,在這種反思中,他把自己也作為反思的對象,客觀地納入到歷史之中。在這方面,他又做到了魯迅先生所說的:解剖別人,同時更嚴厲地解剖自己。更重要的是,他是以面向未來的姿態,開始他對歷史的反思。於是,他超越了個人的恩怨得失,而專注於社會政治體制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與追問。他在總結歷史教訓時,表現得坦誠、敢言、率直而尖銳﹔而在記敘個人遭遇和困厄時,則變得冷靜、超然、委婉而寬容。許多讀者在作家從容不迫的敘事語調背后,感受到心靈的震撼,這種震撼力,首先來自於這位老作家的真誠、坦白、不偽飾、不賣弄、不作秀的人格魅力和堅守科學理性精神的寫作姿態。
而在談到丁玲對自己的影響時,徐光耀說——
“丁玲很喜歡我,看重我,在《昨夜西風凋碧樹》中我引用了她兩封信。一封是我在朝鮮生活時遇到的一些困難和困惑,給她寫信后她的回信﹔一是文研所畢業時,我給她寫了一封信后她的回信,兩封信寫得真好,實在是好。‘反右’時命令我把兩封信上交,我看了感動得不得了,就把原信交上去,自己偷偷抄了一封收起來,那兩封信人人看了都會感動。”
丁玲的信中有幾句話,徐光耀至今難以忘懷。她說:“一時寫不出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輩子寫不好。”徐光耀后來常常拿這幾句話為自己辯護:我寫得不多,但我盡量寫得好。
日 記
徐光耀千萬字日記的出版,無疑會吸引眾多人的眼球。作為文學作家的徐光耀和日記主人的徐光耀,將有什麼不同?
徐光耀回答說——
“我寫日記,純粹是練筆。訓練我的表達能力和文字能力。寫日記完全是赤裸裸的,確實把話說給自己聽。有人偷著看,我會發火,連我老伴看我的日記都很不高興。作為日記的作者,對我在世界上站的位置來說,我是很赤裸裸的,這一點,在文學創作時不可能,寫作要把自己最得意最閃光的地方寫上去。”
而經歷了那麼多次戰爭和各種運動,徐光耀經歷了很多磨難,日記的保存也頗費周折。在他的記憶中,自己是在1941年就開始寫日記了。百姓犒勞軍隊送來一些東西,他得了個日記本,開始寫的時候,一天寫七八句話。
當時,旅長把徐光耀的日記翻開來,笑道:“徐光耀,你把一毛錢買花生也寫進日記了!”徐光耀說:“一個月才一塊錢,拿出十分之一買花生,這就是大事。”
每行軍一次,徐光耀就把所過的村庄都寫上。遺憾的是,后來這本日記丟了,如果保存到今天,就更寶貴了。
徐光耀的日記有幾個基本原則:共識、自願,忠實,准確,完整等。那麼如果完全發表,有些內容會不會在文壇掀起軒然大波?徐光耀難道沒有顧慮嗎?
對此,徐光耀坦率地說:“忠實是肯定的,准確難說,是我的個人眼光,有眼光的局限。我也有顧慮。我把自己和整個歷史亮出來了,對自己有很大的剖析,可能提到的有些人和他們的后代看了不愉快。”
但是,徐光耀想,如果對人們有好處,無妨犧牲自己。在日記的前言裡,他說,我現在認識到,當時認為是人家不好,恰恰是自己不好。我在日記裡也有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的批評。會不會破壞我在讀者心目中的形象,免不了。我不在乎。
對於當下軍事題材的作品“有高原沒有高峰”的現狀,徐光耀也表達了自己的遺憾:“近一百年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現實生活非常復雜、非常豐富,應該是出大作家的時候,但是沒出來。隻能說非常可惜。”
徐光耀很關注當下的抗戰題材作品,但是看了往往失望,還有點生氣。“大部分有點夸張,瞎編亂造,我不同意。在我眼裡不產生真實。我一看就是假的,是編出來,沒一點根據。我也編了《平原烈火》,但是有真實的事跡支撐著。現在作品首先是不真實,不能感動我。”
徐光耀說,如果自己年輕,有一個好題材,題目就是《將軍向我們走來》,這個題材裝了幾十年,現在爛在肚子裡了。人物是他自己非常欣賞的,很活,是用現代的眼光看,不是用過去的眼光看。“要真是寫出來,死也瞑目了。”
有位蘇聯作家說,作家有兩種,一種是用腦構思用手寫﹔一種是隻有拿起筆,故事才能寫出來。徐光耀是第二種。他原來想寫,不是被這個打斷,就是被那個打斷。
現在沒有力氣了,徐光耀覺得很惋惜。
有人想給徐光耀寫傳記,認為他有三大功勞,一是寫了《小兵張嘎》,二是發現了鐵凝,三是寫了《昨夜西風凋碧樹》。徐光耀說:“我自己感覺比較良好的,一是《小兵張嘎》,一是《昨夜西風凋碧樹》。鐵凝不是我發現的。我要真發現了,就真偉大了。”(舒心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為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