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東
2016年11月28日08:25 來源:北京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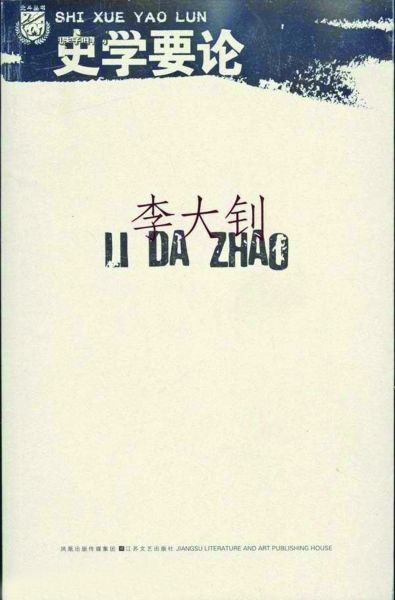

1982年,著名史家白壽彝先生曾撰文指出:“李大釗同志對於史學的崇高的期望,使我們今天讀著他的遺著,還覺汗顏。”姑且不去發微李大釗厚重的史學思想,僅就《史學要論》這本不到四萬字的小冊子而言,白壽彝先生即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史學開辟道路的重要著作”,對於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來說,“李大釗不愧是第一個開辟道路的人。”而且這本小冊子凝結著一個革命家、一個無產階級理論家對人類前途的真摯的希望。時至今日,一版再版的《史學要論》,依然凸顯著李大釗史學思想的價值和地位。然而當下存在的諸種治史風氣,與李大釗對史學的崇高期望還有不小的距離。
社會史研究原本是走出“史學危機”的重要突破口,但卻因“碎片化”的研究取向,而走入另一種 “危機”
改革開放以來,史界學人開始用新的時代眼光去審視史學,“史學危機”的呼聲成為學界重新尋找史學發展道路的一個重要開端。社會史就是當年希望沖出史學危機的重要嘗試。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嘗試似乎又使得史學步入了敬謝不敏、意興闌珊的境地。近年來廣受詬病的“碎片化”現象即是如此。社會史研究重心“下移”,將具體而彌散式的選題作為研究對象,進而出現了七零八落、瑣碎靡遺的研究偏誤。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碎片化”的現象,往往使得“人”在歷史學當中處於屈從的地位。
李大釗明確提出,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而人類社會就是人的生活經歷,人的活動和經歷構成了各種“人事”,是成千上萬的“人事”組成了人類社會生活。李大釗正是以人及“人事”作為史學研究的切入點。在他看來,歷史上的“人事”的產生發展,並非是孤立的單線發展,而是相互聯系的。也就是說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應該是整個的人類社會,絕非是孤立的事件和片段的記錄。因此他特別強調,不能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東西﹔要把人事看作一個整個的,互為因果,互有連鎖的東西去考察他”。人事的變化推移就在於“健行不息”,是“不靜止而不斷的移動的過程”。而時下的“碎片化”研究卻很難完全關照到這個“移動”的過程和有序變化的節奏。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社會史研究原本是走出“史學危機”的重要突破口,但結果不免因“碎片化”的研究取向,而走入另一種“危機”。
過分地通過堆砌資料以“考鏡源流”,實際上是丟棄了李大釗所倡行的“活的歷史”,最終淪為 “僵石”、“枯骨”,成為“死的歷史”
這些年來出現的“碎片化”取向的另一面,是排斥合理的宏大敘事。早在1981年,白壽彝先生就提出:“細小問題的考証,我認為,也可以作,甚至也可以有一部分同志專門去作,但這總不能看做是我們工作上的重點。”他建議史學工作者應重視開闊自己的視野,把天地看得大一些,要站得高些,要有察往知來、承前啟后的抱負,要善於發現重大問題,推動全國史學的前進。但是這種敘事宏大的史論史著,直至目前真正有建樹的似乎並不多見,層出不窮的是“一個村庄”、“一個家族”、“一種疾病”的探究。這種“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研究取向,不僅囿限了人們對歷史的整體認知,而且也限制了人們對重大歷史問題開展探究。結果歷史日益被社會邊緣化,歷史學的影響漸趨式微。
盡管歷史研究是要求“真”,但是絕對的真實是不存在的,那種所謂絕對求“真”只是一廂情願式的幻想。但是現實情況是,不少學人依然寄希望通過史料還原所謂“真實”的歷史。要還原歷史,勢必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式地搜尋史料,通過堆砌資料以“考鏡源流”,希望以此成為歷史研究的最高規則和學術標准。這樣的結果,實際上首先就丟棄了李大釗所倡行的“活的歷史”,最終淪為李大釗所謂的“僵石”、“枯骨”,成為“死的歷史”。歷史研究的僵硬刻板,也就成為李大釗所謂的“空筆”。然而時下的歷史研究,諸如這樣的“空筆”又何其之多,結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普通人對史學的閱讀興趣。實際上最近這幾年一些調查統計已經暴露出這樣的問題。
李大釗特別強調史學致用現實、啟發人生的功能,當前史界最應注重發揚四種精神
在李大釗的史學思想中,特別強調史學致用現實、啟發人生的功能。然而這一問題,即便在今天也沒有成為普遍追求的理念。“為研究而研究”、“為史學而史學”的現象依然存在著。林同濟說,史學是“百學之王、百政之始”。中華民族“用歷史以激發未來——且莫論其所激發者有當與否——恐怕在中國是最有效也最自然的辦法了。”在筆者看來,當前史界最應注重發揚四種精神。
第一,塑造角色意識,承擔社會責任,發揚“出史入道”的精神。如果說歷史是一個國家的民族記憶,史學研究者實際上就擔當著作為民族記憶的代言人的角色。因此,史學研究不僅是史家本身應有的職責,也是史家通過研究歷史與社會國家聯系在一起的實踐形式。史家的角色意識與社會責任,至少在兩個層面會影響到史學的發展趨向,第一是史學的求實精神,第二是史學的經世致用。這樣的角色意識與社會責任,應當成為當前對史學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如果說當年孔子因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麼對於今天的史學工作者,更應該在社會變革轉型的關鍵時期承擔起這樣的責任。總而言之,研究歷史要有“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的精神。
第二,緊握時代脈搏,在社會變革轉型中凸顯大時代精神。在李大釗的史學思想中,“時”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在他看來,一切事物歸根結底都以“時”為轉移,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正確地對待過去與未來、新與舊的關系,要以“時”為標准不斷地棄舊圖新。當前的史學研究同樣應以此為基點來展開。盡管實証是史學的重要特點,但是實証不是史學研究的全部,史學的真正使命恰在於社會變革的過程中,探求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在傾聽時代呼聲的過程中探究史學,在解答時代關切的問題中體現史學應該具有的時代精神。
第三,發掘問題意識,在討論攻克重大問題中激發開拓精神。直面問題開展研究,原本是史家應有的素養,這也是當年李大釗研究史學的重要邏輯起點。但是這些年來的史學研究實在缺乏熱烈而生動的局面,許多應該由史學討論的問題卻“集體失語”,許多該由史學來解決的問題卻“集體出逃”。沒有問題就沒有焦點,沒有焦點就無法聚合力量。研究歷史就是研究矛盾。研究歷史上的各種事件,就是要研究歷史上的各種矛盾,從這些矛盾中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來。“問題是史學研究的強心劑”,我們熱切期望史學工作者,在研究具體問題的同時,也能夠提出重大的史學問題。
第四,注重借鑒吸收,在史學話語中秉持獨立自主的精神。史學是一門綜合性較強的學科,打破史學壁壘,借鑒吸收相鄰學科,亦是李大釗史學思想中的重要觀點。但是任何事物如果走向極端,往往會南轅北轍,走到其相反的方向上去。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全球化背景下,隨波逐流地追逐所謂的新潮理論,逐漸失去中國民族特色的史學研究,致使史學研究缺乏基本的學術增量,更遑論以本土化來回應西方強勢的學術挑戰。史學原本是一個國家的民族記憶,它的最大特點就是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一味地拘泥於西學理論與國外名詞,往往會使史學的民族性失真,缺乏堅實的歷史土壤,而且也是沒有研究效度的。因此,在注重借鑒吸收的過程中,秉持獨立自主的精神,是史界學人需要認真思慮並切實踐行的一種精神。
(作者為天津商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 相關專題 |
| · 李大釗紀念館 |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人民黨建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