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冉 昊
2017年10月27日07:39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
|
嘉興南湖紅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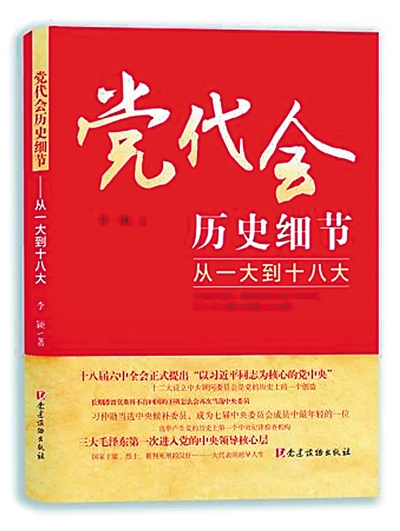 |
|
|
 |
|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 |
至今,中國共產黨已經召開了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細究黨史,會發現有很多疑問有待挖掘。比如,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為何距離六大間隔了整整17年?等等。歷史的謎團往往隱藏在細節之中。黨建讀物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把揭開謎底的鑰匙。
這本書告訴我們,早在1931年1月,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就把召集七大作為全黨“最不可延遲的任務”之一。可為什麼“最不可延遲的任務”變成間隔最久的會議了?一方面,隨著五次“反圍剿”及長征的進行,革命形勢日益嚴峻,抗戰的全面爆發又一次延遲了七大。1938年,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就召開七大“立即進行准備工作”,部分地區選舉了七大代表。1940年,甚至部分代表已經抵達延安。但1941年延安整風運動使得七大日程再次延遲。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完成了召開七大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准備,之后才召開了中共七大會議。
原定的七大會期較短。大會開始后,代表們紛紛要求延長,讓大家有更充分的時間交流和討論。一開50天的七大,成為中國共產黨歷次代表大會中會期最長的一次。
以問題引領敘事
《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的作者李穎是中共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參加過《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等黨史基本著作的撰寫,長期跟蹤研究黨代會歷史。她曾經在文章中講述這樣一個故事:1940年5月,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的長子、時年31歲的李葆華策馬急奔延安,他是中共晉察冀邊區委員會常委兼組織部部長,當選為黨的七大代表。在趕赴盛會的途中,他和戰友遭遇日軍伏擊,一名代表墜入深溝壯烈犧牲。“為了開黨代會,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不同於敘述黨史教科書式的嚴謹或是宏大的歷史敘事,在這本書中,李穎採用了別具一格的方式:篇章全部採用問題的形式,共設計了109個問題。這使原本略顯嚴肅的學術命題立刻脫掉了“陽春白雪”,引發普通讀者的興趣。例如: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沒有參加一大?六大為何遠赴莫斯科召開?八大黨章為什麼沒有提毛澤東思想?凡此種種,使學術問題通俗化、學理研究大眾化,增加了可讀性。
這一個個問題如炮彈一樣打出,直擊讀者內心的各種疑竇。此外,通過重重問題的設置,使本書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特征,在增加文字通俗性的同時,文章的學理價值並沒有絲毫減色。
如果說黨史研究容易陷入大量歷史材料的堆砌和歷史沉渣的篩煉,那麼最新史料的挖掘和最新研究成果的運用,則成為這本書的一大亮點。對於中共六大的敘述,其中一個部分就採用了中央檔案館在2015年編選文獻中的新發現,即在1928年六大會議期間使用的“中共六大會場規則”的原始文本。分“會場秩序”和“議事細則”兩個部分,共列15項要求。議事細則規定得也特別詳細。如“對於討論之發言每人至多三次”,對於政治報告的討論發言,要求第一次至多40分鐘,第二次15分鐘,第三次5分鐘。同時指明:“發言時如涉及討論范圍之外時,值日主席有權制止。”諸如此類的要求,保証了大會的高效進行。
點面相扣 縱橫共振
單就史實的敘述而言,這本書的最大特點是縱橫結合。縱向上說,全書一以貫之的主線是歷次黨代會的順時演進。這根主線基礎上,進一步衍生出幾條縱向的支線。一是黨的組織建設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如監察制度的從無到有,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逐漸加強﹔二是黨的基本理論體系如何通過黨代會不斷充實和完善,如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提出,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系統闡明,再到“市場經濟”表述的正式確立等。
橫向上說,本書將歷次黨代會放到了整個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中進行敘述,既包括黨代會召開的國內外政治背景、也包括其所處的社會和階級基礎,這樣一來,對歷史事件的敘述,層次分明而時代感厚重。如中共五大之后,翌年即召開中共六大,其重要的歷史背景在於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全面破裂以及中共中央自身的改組等重大事件的出現﹔而中共七大到八大之間之所以間隔11年,與黨和國家經歷了國家性質和基本制度的兩個重大變革有直接關系。
由此,歷史縱向發展與時代橫截面的結合,形成了對歷次黨代會敘事的點面相扣和縱橫共振,奏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仁人志士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時代強音。
黨代會的歷史轉折作用
過去我們往往注意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歷史轉折作用(如十八屆三中全會),而忽視了黨代會全會本身在歷史中的重大轉折作用——它集中表現為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制度性轉折和對時代所起的歷史性轉折。
一是中國共產黨自身不斷發展和完善過程中的制度性轉折。如1923年的中共三大專設了“中央局秘書”一職,實際上相當於后來設中央主席時的總書記,並具有部分黨中央“秘書長”的功能,規定“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和秘書簽字”,它體現了新生的中國共產黨開始通過黨內不同職務之功能權界的劃分,對黨內最高領導權力加以制約的初步探索。
又如1927年中共五大選舉產生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監察機構,即中央監察委員會。雖然中共一大綱領和二大相關決議都有對黨員行為進行監督的規定,但直到五大正式建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才真正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各級黨員領導干部的監督實現了常態化和制度化,使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及黨紀黨法的權威第一次有了相應的機構作為保証。
再如在中央組織制度方面,1982年中共十二大不再設主席和副主席,隻設黨中央的總書記,並由總書記負責召集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議,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實踐表明,如果主席制度和總書記制度同時存在,往往導致其中一個有名無實,而當主席和總書記由一人兼任時會產生制度性問題。
二是多次黨代會所發揮的時代性轉折效應。我們知道,中共早期的發展歷程,都打上了深刻的共產國際烙印。甚至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到六大,也無一例外地受到共產國際的指導,也有共產國際代表參加。而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是第一次沒有共產國際參與的黨代會。這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也不再接受任何外國黨或國際組織的指導。中共七大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召開的黨代會,有關黨代會的一切重要問題都由中國共產黨自己做主,因而具有劃時代意義。
將近半個世紀之后,上世紀90年代初,社會思潮更迭,是繼續推進市場,還是重新回到計劃?人心不定。199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以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為指導,明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打消了很多人的顧慮。鄧小平同志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成為有膽魄之人開荒進取的“尚方寶劍”。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為中國經濟后來20余年的持續騰飛奠定了堅實基礎。
恩格斯曾言,歷史是我們的一切。而中國共產黨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歷史,則是黨不斷自我完善和推動時代發展的一切具象,是中國共產黨、國家乃至民族由弱小變強大、歷曲折而彌堅的生動畫卷。
生存與死亡,忠誠與背叛,信念與放棄,皆成為這個歷史大熔爐中的一粒粒火星,一閃之后迅疾消逝於灰燼之中,我們怎能不細細察之?!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副教授、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推薦閱讀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黨史學習教育”官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