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4月04日10:14 來源:重慶日報

聶榮臻(1899-1992),四川省江津縣(今重慶市江津區)人,著名軍事家、政治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192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19年10月赴法國勤工儉學,1924年到蘇聯學習。

江竹筠(1920-1949),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6月被捕關押在重慶中統集中營,1949年11月14日被害於歌樂山電台嵐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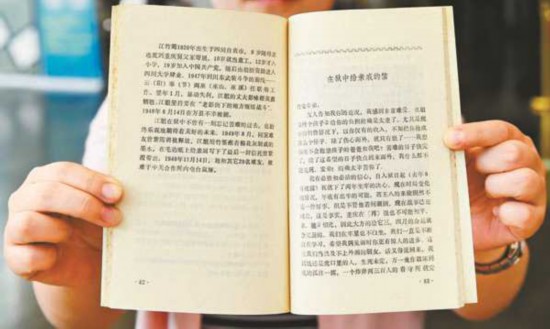
江竹筠烈士在獄中寫給親戚的信。記者 熊明 攝

劉願庵(1895-1930),原名劉孝友,字堅予,曾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1930年被捕,5月8日在重慶巴縣衙門口犧牲,年僅35歲。
核心提示
“人間三月芳菲始,又是一年清明時。”清明時節,人們在祭掃祖墓、追思先人的同時,也沒有忘記無數為了人民幸福、民族解放和國家富強,奮斗一生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今天,我們更應緬懷先烈,傳承其精神、信仰和價值觀。
今天,就讓我們看看他們寫給父母、兒女、兄弟姐妹、親朋好友以及黨組織的肺腑之言。在字裡行間,感受到他們在那段苦難歲月裡的精神信仰和家國情懷。
聶榮臻寫給舅舅的家書——
對國家有利國利民之責任
1919年10月,聶榮臻赴法國勤工儉學。在法期間,聶榮臻多次與江津家人——父母及舅舅通信。這封家書是聶榮臻赴法國勤工儉學時寫給舅舅的,家書文辭儒雅,書法遒勁,顯示了年僅二十出頭的聶榮臻的文化素養及家教涵養。
舅父大人尊鑒:
語雲:光陰似剪(箭),日月如梭。誠哉斯言。回想拜別,曾幾何時,於茲盈之半載,定期數年,亦轉瞬間耳。然遠天涯,孺慕知深,是以舅之情未嘗一日忘之,恭惟起居萬福,為頌為慰。
甥曾稟所次,諒已達座,至各種情形,家書中言之亦詳,諒大人亦悉矣,故甥無再贅。
惟法國經歐戰后,雖極圖恢復,然不無一般淒涼景況,堂堂華宇,三煙無炊,通衢大道,行人絕跡,惟於鐵道之火車上下往來而已,且一般人民除老弱婦女外,即見斷手缺足之廢人。以甥現住之獨魯公學而論,八個教員五個跛,三個教員四隻手。甥觀此景,心為之膽寒。
甥雖在法國,然各國之大勢,亦頗得識,因我國在巴黎開有《學生周刊》,並於都爾設有印刷局。
現在各國都有內亂,日本已大鬧革命,德國自歐戰后,改專制為共和國體,現德皇又復辟,與我國之國體無異,未知帝制能否成立?恐將來歐洲戰爭復起,並日本與美國,亦有宣戰之機,將來世界上,必有一大戰爭而后已。
甥觀中華尚有偷閑之日,然國勢之不如人,學問之不如人,亦自愧也。甥曾處鄉裡,不識世界為何物,及游地球大半,經有許多地面,強國弱國,顯然分矣。回思祖國,號稱文明古邦,然不及外人亦遠矣。
甥嘗思之,閑居家庭,優游終生,亦自樂也,既曰出國,則負無窮之責任焉。對於身,則有求生活之責任﹔對於家,則有事父母畜妻室之責任﹔對於社會,則有扶救之責任﹔對於國,則有利國利民之責任。
故甥無時可得稍懈,欲如前日之承歡尊前,無可得耶。隻得修書呈稟,以敘甥恨而已。乞望大人常常指示為盼。
並甥與國平老表組織求學之計,大人以為何如?蓋甥有不得不然之勢,家中不可以洽親戚,無可告求,不自謀自給而何?且甥亦替家嚴設想,若以讀書而負債,使父母不得安寧,亦非甥所為。
要之,甥有國平老表同行,彼此皆可謂幸矣。
言不盡意,字跡不裝,勿使外人閱。
敬稟崇安
民國九年三月十八號 外甥聶榮臻謹稟
責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據了解,目前,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珍藏有聶榮臻留法勤工儉學期間家書共計8封。寫於1920年和1922年,分別為毛筆和鋼筆書寫。
據了解,聶榮臻的8封家書是1982年重慶長江航運公司基建工程處魏澤均先生捐獻給重慶市博物館的,現藏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這封家書是聶榮臻離開家鄉后半年左右,寫給舅舅的信,從中可見甥舅感情至深,更見其報國之志。”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研究館員胡昌健對這封家書進行了解讀。
從信中首先可以看出,剛剛出國的年輕聶榮臻見了世面,感到了祖國的落后。信中說:“甥曾處鄉裡,不識世界為何物,及游地球大半,經有許多地面,強國弱國,顯然分矣。回思祖國,號稱文明古邦,然不及外人亦遠矣。”
然后,因為祖國的落后,聶榮臻油然而生“責任感和使命感”。他的責任感,是對自己、對父母妻室、對祖國的責任,他不是出國去玩兒的。信中說:“既曰出國,則負無窮之責任焉。對於身,則有求生活之責任﹔對於家,則有事父母畜妻室之責任﹔對於社會,則有扶救之責任﹔對於國,則有利國利民之責任。”
其三,表達了自立自強的意願。在法國生活,必然有經費付出,年輕的聶榮臻不願意給父母增加經濟負擔,自我感到“有不得不然之勢”,“不自謀自給而何”?於是“與國平老表組織求學”。這也是他為父親著想,決不能因為自己出國讀書而致父親“負債”,他說:“甥亦替家嚴設想,若以讀書而負債,使父母不得安寧,亦非甥所為”。
胡昌健說,這封家書對今天的我們有非常積極教育意義,“從中我們可以學到如何為人子,為人父母,如何擔當責任,為領導干部如何明大德、守公德、講政德做了很好的示范。”
江竹筠又一封家書首度公開——
孩子吃得飽穿得暖足也
這封首度公開的家書是1948年4月1日江竹筠寫給丈夫彭詠梧前妻弟譚竹安的,20世紀80年代譚竹安捐獻給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管理處,現藏重慶紅岩革命歷史博物館。全文如下:
竹安弟:
你三月二十四日的信我收到了謝謝你。信給了我溫馨,也給了我鼓勵,我把它看了兩次,的確,我感到非常的愉快。
由於生活不定,心緒也就不安,腦海裡常常苦惱著一些不必要的幻想。他,是越來越不能忘了,雲兒也成了我時刻惦記的對象。
我感謝你和其他的朋友,雲兒是生龍活虎的,我知道他會這樣在你們的撫育之下,他是會健康而愉快的成長的。可是,我不願意他過多的耗費你們的金錢和時間,吃得飽、穿得暖足也,可別嬌養,但是得特別注意他的病痛。春天來了得嚴防腦膜炎。
幺姐,也成了我不能忘記的人物。可是我能給她一些甚麼幫助呢?我想去看她,而且很想在春假裡去,但是又有多大的好處啊?除了感情上大家得到一些安慰而外,而且,我的身子多病,恐怕在路上出毛病,所以去不去都叫我很難決定。要是陳援她們那個托兒所能夠組成,幺姐能在那兒幫幫忙的話,那是最理想的了。你和朋友們給她一些教育,她就會走上正路的,你說是嗎?我知道她會像親生的孩子一樣的愛雲兒,就像我對炳忠一樣,基於人類的真誠的愛是不能否認的,我尤要接收,更何況她的孩子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孩子的父親呢?是吧!我答應給他們通信,但是我並沒有寫,我不知道該寫些甚麼?
四哥死后,家裡的情況仍舊很好,但是由於鬧匪的原因,家裡人都很累很苦,你回家,我恐怕你吃不消,不過,我可以問問,要家裡人同意而且需要的話,我再告訴你,我想機會有的是,不過,你既然叫幺姐來,你又要回家,這怎麼好辦呢?願能考慮、考慮!
重慶隻有你給我通信,其他的沒有,我也不要,因此通信處別給他們。
真的,我走時曾托李表兄來看你,他來過嗎?
握別
你好
竹姐 1/4
一個真實的人的心路表白
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周勇教授說,第一次讀到這封信,感覺這與我心中的“江姐”有相當的距離。但反復誦讀,讀出了一個真實的“江姐”。
這封信寫於1948年4月1日,當時江竹筠正在重慶從事地下工作。
收信人譚竹安,其姐譚正倫是彭詠梧的前妻。
江竹筠在信中首先表達了對親友的感情,對犧牲了的丈夫彭詠梧和兒子彭雲的思念——“由於生活不定,心緒也就不安,腦海裡常常苦惱著一些不必要的幻想。他,是越來越不能忘了,雲兒也成了我時刻惦記的對象。”
她感謝親友對彭雲的照顧,也囑咐親友不要嬌養孩子——“我不願意他過多的耗費你們的金錢和時間,吃得飽、穿得暖足也,可別嬌養”。
這封信用比較多的篇幅表達了對彭詠梧前妻譚正倫復雜而真實的心路。想見,又怕見的心情——“幺姐,也成了我不能忘記的人物。”這裡的“幺姐”即譚正倫。“可是我能給她一些甚麼幫助呢?我想去看她,而且很想在春假裡去,但是又有多大的好處呢?”
但是,她對“幺姐”又是坦誠的,“我知道她會像親生的孩子一樣的愛雲兒,就像我對炳忠一樣,基於人類的真誠的愛是不能否認的,我尤要接收,更何況她的孩子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孩子的父親呢?”這裡的“雲兒”即江竹筠與彭詠梧之子彭雲﹔“炳忠”即彭詠梧與譚正倫之子彭炳忠。
周勇說,這封信寫於1948年4月1日。兩個月后,江竹筠被捕,一年半后犧牲。后來,譚正倫以無私的愛,把彭炳忠和彭雲撫養成人,實現了江竹筠的遺願。江姐這封家書通篇表達了對丈夫的深切緬懷,對兒子的無限牽挂,對彭詠梧前妻的坦誠與糾結,“這是一個在特殊歷史時期和歷史環境中的女人、妻子的真實心路,一個身為共產黨員,但同時也是一個真實的人的心路表白。”
劉願庵寫給表姐夫的遺書——
此身純為被壓迫者犧牲 非有絲毫個人企圖
1930年5月8日,重慶城內巴縣衙門前院壩裡響起一陣尖利的槍聲,三名共產黨人應聲倒地,被軍閥劉湘下令槍殺。
槍響之前,三名共產黨人呼喊口號。其中一人,積蓄生命中最后的力量呼出口號之時,一腔鮮血驟然從口中噴出,濺到了照壁上。這個人就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四川省委書記劉願庵。
重慶日報記者得到的這封家書,便是出自劉願庵之手。
“這封信是劉願庵被捕入獄,得知自己即將被處決后寫給表姐夫周竹虛的遺書。”周勇介紹,這封信1979年由成都周世模捐獻重慶市博物館,現藏三峽博物館。
重慶日報記者看到,這封遺書僅有1頁,長29厘米,寬24厘米,毛筆書寫,全文行文流暢,一氣呵成,讀來令人蕩氣回腸。遺書全文如下:
竹虛大哥賜鑒:
弟之行動始終不能為兄贊同,而弟亦不能如兄歷年諄諄勸告放棄工作。然而兄始終對弟之愛護有加,及對於舍間之照拂,實永藏心中不敢或忘。茲當永訣,念及今世不能有所圖報,實深歉仄。所可以自慰者,此身純為被壓迫者犧牲,非有絲毫個人企圖,素為兄所深知,必能諒解,而不致如一般倫夫走狗之責毀,或者此亦所以報德者也。舍間狀況不待言而為兄所盡悉,敢以累兄時加顧助,以待弱弟妹之成立。此外弟孑然一身,毫無系累,亦別無所求。至弟之尸體,已囑送之醫院解剖,以盡我最后對人類之貢獻,萬望無加阻止,虛耗金錢。寄弟婦遺函一封,務請設法轉寄,勿任遺失,至所盼望。弟之死耗,對舍間務請秘密,勿使老親知之,即以弟已出川代為掩蓋。四姊處亦望勸其勿過悲傷,人生誰有不死,弟今日之死,雖不能說成仁取義,亦較困死牖下多多矣。臨穎倫(愴)神,欲言不盡。
即頌
起居多福,諸維諒察。
弟友遺書
舊友多不願往托,如均逸、君彤等,人情冷暖,托之無益,惟兄可酌商之。
無聲的力量跨越時代
“這封家書實際上是劉願庵對理念信念的總結,對自己后事的交代。”周勇對這封家書進行了進一步的解讀。
首先,這封家書開頭表達了劉願庵對兄長關愛自己的感謝之情。也對因心有信念,參加革命,故不能聽從兄之放棄革命理想的勸告的表白——“弟之行動始終不能為兄贊同,而弟亦不能如兄歷年諄諄勸告放棄工作。然而兄始終對弟之愛護有加,及對於舍間之照拂,實永藏心中不敢或忘。”
全信最大篇幅是對家人和自已后事的交待:
對弟妹:囑托兄長照顧弟妹的成長——“敢以累兄時加顧助,以待弱弟妹之成立。”
對父母:囑托兄長不要將自己犧牲的消息告訴父母,就對他們說自己出遠門了。——“弟之死耗,對舍間務請秘密,勿使老親知之,即以弟已出川代為掩蓋。”
對妻子:囑托兄長將遺書送達妻子—“寄弟婦遺函一封,務請設法轉寄,勿任遺失,至所盼望。”
對遺體:表達了自己捐獻遺體對人類做最后貢獻的願望——“此外弟孑然一身,毫無系累,亦別無所求。至弟之尸體,已囑送之醫院解剖,以盡我最后對人類之貢獻,萬望無加阻止,虛耗金錢。”
遺書最后表達了劉願庵舍身取義的決心——“人生誰有不死,弟今日之死,雖不能說成仁取義,亦較困死牖下多多矣。”
周勇說,信中的一句話尤為催人淚下,“此身純為被壓迫者犧牲,非有絲毫個人企圖。”這是劉願庵對自己一生的總結,也是他一生奮斗的唯一目的,也可以說這就是劉願庵的中國夢。
據周勇透露,劉願庵在給妻子周敦琬(四川省委委員、省委秘書機關負責人)的遺書中更傾訴了一個革命者在臨刑前感天動地的愛情:你要“把全部的精神,全部愛我的精神,灌注在我們的事業上,不要一刻懈怠、消極”,“別了,親愛的,我的情人,不要傷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靈,時刻是望著中國革命成功,而你是這中間一個努力工作的戰斗員!”
周勇說,“從這些直抒胸臆的家書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歷史的溫度,看到那些付諸筆端的信仰的光芒。這對今天的人來說,恐怕很難理解。但這就是活生生的歷史。它讓我們可以更直觀地洞察先輩們的理想與初心,這種無聲的力量,跨越時代,照耀當下,激勵我們努力工作。”
(記者匡麗娜、實習生蒲婷)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人民黨建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