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2018年12月24日09:38 來源:北京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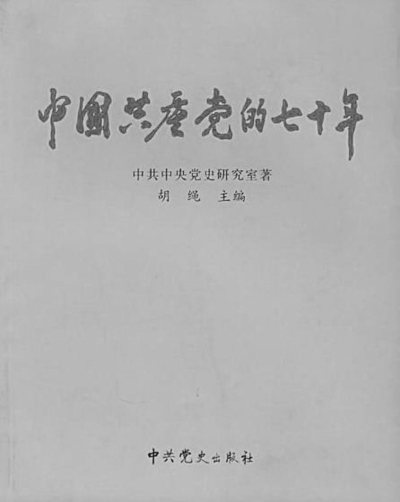
胡繩一生著書立說甚多,代表著作有《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等,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印數達數百萬冊。此外,還發表了大量政論性學術論文。
胡繩(原名項志逖)是我們黨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歷史學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開創者和中共黨史學的奠基人之一,可以說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學界大師,終其一生,用其《八十初度》中的詩句來說,可謂“塵凡多變敢求真”。
早慧的天賦+勤奮的筆耕+追求進步的砥礪,奠定了胡繩成為大師的基礎
2000年11月胡繩逝世時,新華社發表經中央審定的胡繩生平說:他少年早慧,嶄露才華,又能不斷刻苦自勵,辛勤勞作,終於鍛煉成為學識淵博、成就卓著、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學者。這是對胡繩早年情況的評介。像這樣的評介,在當代中國其他重要人物的生平中罕見。但這正是胡繩不同於一般常人的特質。
胡繩1918年1月出生。由於家庭為書香門第,兒時從父教讀已一二年,在1925年7歲入小學時即讀五年級。9歲就讀蘇州中學初中部,10歲開始寫詩,12歲向葉聖陶主編的《中學生》投稿,兩年間自由體詩作達30首,被稱為“神童”。但他又不同於那種有怪癖的“神童”,在學校跟其他同學一起積極投入社會活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他讀高中,參加學校“反日救國會”演講團,多次上街宣講抗日。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后,他開始接觸包括宣傳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社會科學書籍和中共內部報刊,並擔任了所在高中學生會主席。
國家的危難狀態震撼著當時的進步青年。胡繩跟一些同學交流對中國命運和前途的看法,既有擔心也寄予希望﹔他知道蘇聯在世界被壓迫人民斗爭中的地位,並懷有真切的向往之心。他讀了一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還有《共產主義ABC》等,被馬克思主義所吸引。他也讀過瞿秋白的一些書,了解到中國共產黨經歷過並正在進行著艱苦斗爭,也被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所吸引。這樣的進步傾向奠定了青年時代胡繩的生活和思想基礎。
胡繩15歲時,與人合作主編《百合》月刊,在創刊號上發表的長文署之以“胡繩”筆名,從此沿用終生。16歲進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成了“少年大學生”。他在上大學期間,不是一個死讀書的學生,揀可聽的課聽之﹔不愛聽的,就跑到北海旁的圖書館找點書看看。他在大學讀了一年之后,想換一種生活方式,離開北大去上海,開始了同現在一些人“北漂”一樣的“上漂”生活。
1938年胡繩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從自由人到“黨的人”的新征程
“上漂”是胡繩成長史的一個重要節點。他步入社會,開始了解社會的多棱鏡。他一面讀書自修、一面從事寫作,並參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化宣傳,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在上海兩年間,他為《讀書生活》《生活知識》《新知識》《自修大學》《時事新報》等報刊撰稿,參加《新學識》的編輯工作,發表了60多篇文章。他的生活完全靠寫文章的稿酬維持,沒有去找什麼正式工作。1935年秋,經從事世界語研究的葉籟士介紹,胡繩參加中共“文總”(左翼文化總同盟)領導的“語聯”(中國普羅世界語者聯盟,上海世界語者協會是其公開機構,是中共的外圍組織)工作,並短期擔任上海世界語者協會機關刊物《世界》的編輯,寫過若干有關世界語和語文問題的文章。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在此期間,結識了胡喬木。當時,胡喬木是黨在文化工作上的領導機構“文總”的負責人之一,胡繩參加的“語聯”只是黨的外圍組織。對於進步青年來說,與胡喬木建立了聯系,就等於找到了黨。胡喬木找過胡繩幾次,談了一些對文字改革和拉丁化方案的意見,使胡繩感到喬木對文字音韻學很有些知識。但兩人認識沒多久,胡喬木就離開上海去了延安。此后,胡繩參加的文化活動更多。北京爆發一二·九運動后,他還參加了上海聲援北京的游行示威和抗日救亡的集會活動。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戰開始后,胡繩到達武漢從事文化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直至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在武漢期間,他主編通俗刊物《救中國》周刊,起初大多自己撰稿﹔受邀參加柳湜創辦的《全民周刊》編輯工作﹔發表了數十篇文章。“上漂”以來,他一直沒有停下手中的筆,不斷地寫呀寫,3年中,發表了100多篇文章,出了近10本小冊子。1938年1月,胡繩加入了多年追隨的中國共產黨。由於過去做了不少文化工作,黨組織決定他不需要候補期,入黨后即是正式黨員。這既是對胡繩過去努力的認可,也是胡繩人生道路的新裡程碑。他開始了從自由人到“黨的人”的新征程。
三本書成就了胡繩作為大師的晚年輝煌
在我們黨內,從新中國成立直至20世紀末的半個世紀內,長期參與中央的文字工作,起草中央重要文件和重要講話的“大秀才”不少。但是,成為黨的兩代核心領導的“一支筆”者,第一是胡喬木,第二就數胡繩了。
新中國成立后,胡繩就走上了黨和國家思想文化部門的領導崗位,而且逐步地走向核心部門。他先后擔任過中央宣傳部《學習》雜志社主編、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紅旗》雜志社副總編輯。按照現在的話說,這都是中央的重要智庫。在這些部門工作,無疑會參與為中央服務的重要文字工作和相關活動。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間,胡繩參與了許多中央重要政治文件和理論文獻的起草和修改,參加了毛澤東和黨中央召集的一些重要學術理論問題的討論。胡繩從“文化大革命”發動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期遭受的挫折和復出后參與中央的文字工作。
胡繩八十自壽銘寫道:“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載。”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前后,還在他的“惑而不解”時期。這時的“惑而不解”,就是他的思想沒能跟上時代發展。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閉幕講話,促使胡繩的思想不斷解放,逐漸走出思想僵化狀態。“筆杆子”畢竟是“筆杆子”,思想通了,就“惑而有解”。改革開放以后,他又是黨內很難離得開的“一支筆”,不僅參加中央文件和領導人講話的起草討論,而且起著帶一些徒弟的作用,使一批批年輕人也成為了中央的“筆杆子”。
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半個多世紀裡,胡繩的成就,說得直白一點,有如 “雙頭鷹”。一“頭”是我們黨兩代領導核心的“一支筆”,為黨的重要文獻的形成和闡述,為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另一“頭”是個人著書立說,在以《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為代表的研究成果和新中國成立后繼續對近代史展開專題研究的基礎上,20世紀70年代中期,尚且身處逆境的胡繩就開始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部巨著的寫作。90年代,胡繩在組織編修《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的同時,主編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這一印數達數百萬冊的皇皇巨著。此外,正值“粗知天命”(胡繩自謂“七十八十,粗知天命”)之時,胡繩發表了大量政論性學術論文,匯集成《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出版,被譽為“很有影響、很有深度、很有新意”、達到“中國社會科學最高水平”的力作。這三本書成就了胡繩作為大師的晚年輝煌。
(作者為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人民黨建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