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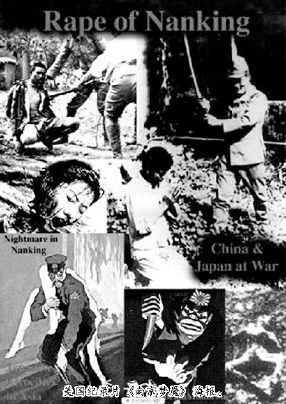
美国纪录片《南京梦魇》海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目的之一是“营造”恐怖气氛,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他们的杀人、强奸、抢劫、纵火犯罪均是以特别的方式进行加害。因此,在日军和暴力等“显性”研究之外,有必要目光延伸到受害者、特别是女性受害者的“心理创伤”研究上,从而使我们关注到那些比较“隐性”的层面。
本文通过爬梳文献和幸存者调查,整合出由南京大屠杀的恐怖和暴力引发的目击者、幸存者和受害者的综合症状,已超出了过去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和理解。
初步研究表明,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精神伤害是广泛存在的。从受害对象来说,不仅有那些直接承受日军暴力的人,也有那些目睹暴行的人;从受害范围来说,不仅有南京人、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从受害时间来说,不仅是经历南京大屠杀的当时,也延续到今天。在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是当今世界必须正视的、属于全人类的历史。
通过本文,可以体会到南京大屠杀给人类心灵造成的伤害。
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长达6个星期,施暴者日本军人与南京居民直接接触,枪声不断,大火旬日不熄,被害者尸体随处可见。而且,有证据表明,日军以特别的方式进行加害,以“营造”恐怖气氛,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
经过“设计”的暴行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日记中记载:“看到遍地是女尸,有的阴道里戳着竹竿,人们会恶心得透不过气来。”德国使馆驻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我的英国同行、领事普里多·布龙,英国武官洛瓦特·弗雷泽和英国空军武官温·沃尔泽在察看英美烟草公司帕森斯先生的住宅时发现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个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位妇女的躯体。”
军医蒋公榖大屠杀期间躲藏于美国大使馆,他在《陷京三月记》中记述道:“最残酷的莫过于活埋了。悲惨的哀号,那人类生命中最后挣扎出来的一种尖锐的无望的呼声,抖散在波动的空气里,远在数里以外,我们犹可隐隐地听得。”
尤其可恶的是,日军在实施暴力犯罪时,常常故意强迫南京市民在一旁观看。《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称:“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家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同谋犯把受害者丈夫或父亲拘留,并迫使这些人充当他们败坏自己家庭名誉见证人的情况屡见不鲜。”
当时,藏匿在意大利驻南京总领事馆的教导总队辎重营长郭歧在《陷都血泪录(节录)》中记述道:
那一天,隔壁洋楼门外来了几十名鬼子兵,领章有黑有黄,但却既无部队番号,又无官长……先把大客厅里的男人统统撵走,再将半老徐娘们拉了过来,当着小孩子的面,光天化日,明目张胆,就在大客厅里,把半老徐娘们的衣裳剥得精光,然后集体演出丑剧,三对一,五对一,去而复来,周而复始……孩子们几回见过这种骇人的场面,一个个的全都吓哭了……客厅外,庭院里,那些女人们的丈夫们,一个个失魂落魄,面红耳赤。有人伏在墙上,哀哀地哭,有人双手抱头,木立不动……一个兽欲已达,裤带犹未系好的鬼子兵快步走出门来,上了大街,又遇见了一队鬼子兵,又是好几十名……这一批紧跟着又一哄而入……
无休止的暴力,使南京居民饱受折磨,《拉贝日记》记载:“人们觉得自己像个重病人,以恐惧的目光注视着时针走动,觉得它走得太慢了,一天好像有100个小时而不是24小时,没有谁知道自己何时会康复。”
中国人作为暴力犯罪对象觉得恐怖,处于中立地位的西方目击者同样如此,1937年12月17日,日军闯入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号称要搜查中国士兵,负责管理该校的美国籍人士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计谋:把负责人困在前门,由三四个士兵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时间似乎凝固了,在恐惧中我们长时间没敢动。”
失去反应能力
南京浦口村民黄学文是个“幸运”者,1937年12月15日,日军到他们村子,把几十人集中起来,从中找手上有老茧等可疑迹象的,一共挑出5名男子。其中一个是瘸子,被释放了;黄学文的父母和妻子抱住日军的大腿求饶,最后被释放;其余3人,因为是外乡“跑反”(方言:指战争时到外乡避难)的,无人出面求情,均被枪杀。那一天下午,天气很好,“太阳晃晃的”。日复一日,在乡间过着贫穷而简单生活的黄学文何曾见过杀人的场面?他遭遇的应激障碍甚至超出专家们的描述,“我当时被吓得眼发黑,什么都看不见,大白天就像晚上一样”,“只听到有枪响”。黄学文没有多少文化,他当然不知道何谓精神伤害,69年过去,他说起日军,只有“害怕”两个字。(《黄学文口述》,调查者:邱伟、胡凌、孙香梅)
因为极度惊恐,南京市民畏缩在一起,像待宰的羔羊。拉贝记录了他家附近一条巷子的惨状:“下水道里3天来也已塞满了好多具尸体。见此情况,人们不禁恶心地浑身颤抖。在院子里,许多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失措的双眼沉默地相互依偎在一起,一半是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他们不敢有所作为,只是希望拉贝这个“洋鬼子”能赶走日军。
对危险极为冷漠
时间长了以后,南京市民对显而易见的危险表现得极为冷漠,在拉贝家避难的南京居民就是如此:“经历了日本士兵带来的苦难后,人们对空袭的危险已变得无动于衷了。成群结队的难民默默地站在院子里,眼睛望着飞机,有些人对飞机不屑一顾,而是从容不迫地在草屋里做他们的事。”
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德国、日本居民身上同样如此。
更有甚者,长时间被暴力和恐惧震慑,有些南京市民失去了人格和起码的自尊,1938年1月2日,日本妇女国防会的几个人到南京来粉饰太平,魏特琳带领她们参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说:“那三个女鬼走时拿出几个霉苹果和一点糖,那些中年难民围着要、抢着要,她们手上拿着几个铜板,在她们手上抢,简直把中国人脸都丢完了。”
精神疲劳和失忆
乔治·菲奇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安全区官员之一,1938年春天,他携带约翰·马吉拍摄的记录电影返回美国向公众宣讲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时,经历了无以言状的失忆,他在《关于菲奇就南京事件进行的巡回演讲》中说:“在演讲的中途,我的心成了一片空白。我想不起来自己在哪里?接下来要说什么?幸亏我想起来带来影片的事儿,我想如果把它放映的话,也许能讲一讲的。这总算顺利过去了,但是最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回到我妻子帕萨迪纳的公寓。”
在另一次集会上,正在演讲的乔治·菲奇碰到了同样的事情,而且由于没带影片去,茫然失措的他只好“结结巴巴地讲到了结尾”。X光检查显示,他的脑部并无问题,于是,菲奇自我诊断说,“在南京的每天的可怕记忆也许同我这神经性疲劳有些关系。”
歇斯底里精神失常
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提尔是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之一,他在《寄往德国驻华大使馆(汉口)的报告》一文中记载了灾难降临时一位中国士兵的失常行为:
随着日军搜查网的收紧,有些士兵因为恐怖而精神失常了。我曾经看见一名士兵用蛮力抢来一辆自行车,鲁莽地朝着在前方数百码的地方前进的日本军队猛冲过去。在路上的行人告诉他这很危险之后,他又突然掉头向相反方向猛冲。他突然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撞到了一个市民身上。最后我看到他一边脱自己的军服,一边想去剥那个市民的衣服。有的士兵则骑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乱跑,对着天空胡乱开枪。留在市内的仅有的几个外国人之一、一个身强力壮的德国人决定教训他一下,就把那个男的从马上拉了下来,夺过他的手枪,朝他脸上打了一拳。那人叫也没叫一声,承受了这一拳。
市民更加惊恐,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记录了日军的抢劫造成的后果:“穷人的食物都被抢光了,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的惊恐之中。”德国驻华使馆南京办事处行政秘书沙尔芬贝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记录了另一个案:“可惜这支占领军又进行了轮换,用年轻的新兵替换全体老兵,遗憾的是仍然发生很多抢劫、强奸以及与此有关的谋杀事件。19号房子附近住着一位精神错乱的母亲,我们朝向边上的那扇窗子不能开,她总是大声哀嚎着:‘杨姑子,小孩子啊!’听了让人忍受不了。”
1938年3月28日的汉口《大公报》引用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在《暴敌兽行世界彰闻英报揭露敌兵狰狞面目》一文中也记载了“难民均患精神性的恐怖病”的事实。
自杀
在南京汤山一带工作的福音传教士卢小庭在日军到来之前就很悲观,日军占领南京后,“他显示了良好的助人及无私的精神品质”,但他显然无力从悲观情绪中自拔,在与美国牧师福斯特和马吉谈话中,表达了以死来抗争黑暗社会的想法,福斯特奉劝他:基督教的观点是活着而不是死去。但1937年12月31日一早,他出了门,留给福斯特一张便条、一首小诗和他的钱包,在《致妻子函》中,他说:上帝不会把他的自杀视为罪过。
这不是个案,遭受凌辱的妇女,更加容易选择自杀结束痛苦。美国传教士马吉的纪录电影中,一个被抓住充当日军“慰安妇”的15岁姑娘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她认识的一个同时从芜湖抓来的女孩子自杀了,她还听说其他人也有自杀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受害者PTSD研究——以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为中心”阶段性成果,本报发表时有删节。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