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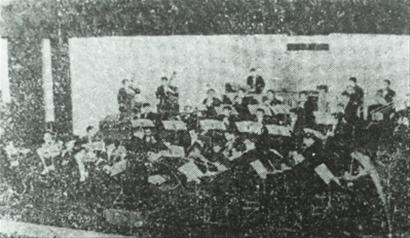
1939年“新京交响乐团”在协和会馆演出。

“新京大同公园音乐堂”旧址。

“乐员养成所”第一期部分学员与老师。
6月17日下午,记者来到沈阳音乐学院。校园里,不少背着提琴的学生与记者擦肩而过。走到第一教学楼楼下,里面传来阵阵钢琴演奏声和歌声。
然而,在70多年前的东北,中国人想自由自在地歌唱可没那么容易。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史教研室副教授马颖,向记者讲述了在1931年至1945年的14年间,日本如何利用音乐来实施殖民统治,以及中国人所进行的激烈反抗。
教材和曲目都是指定的
在日本殖民时期,东北的音乐教育与其他学科一样由日伪当局把持。
日本殖民者不但对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师范学校音乐班和中小学音乐课实行垄断管理,还对教材和曲目进行指定。
马颖告诉记者,当年,东北较有影响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有“宫内府乐队学员班”和“新京音乐院乐员养成所”等。
日本侵略者将原伪皇宫的 “宫内府乐队”进行改组,于1935年开始招收15岁以下的学生,教授西洋管弦乐器演奏。“学员班”设在宫内府西侧的三合大院,先后招收了4期学员52人。学员的学习是在令人窒息的氛围下进行的,稍有差错,日本教师便拳打脚踢,如有反抗,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日本殖民者兴办师范教育,企图通过培养师资力量,将奴化教育渗透到各个领域。当时,师范学校设音乐班的只有吉林市的“男子师道大学”和长春市的“女子师道大学”。音乐班的教材多数为日本人编写和印刷,教师也几乎都是日本人。
而对中小学生来说,日本人更是把音乐教育作为巩固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日伪当局对音乐课的要求是 “音乐以能使唱平易之歌曲度养成美感以资涵养德行为要旨”。1933年5月起,日伪当局对伪满洲国小学进行整顿并规定统一的教学内容、统编教材。音乐课每周上一节或与体育课每周共上三节。中学音乐课每周一节到两节。
音乐奴化教育的危害有多大?马颖说:“我姥姥曾在沈阳读高小。对于那时学的日本歌曲,她一直记得。”马颖小时候,姥姥还曾教她哼唱日本民谣《樱花》。
音乐与政治紧密结合
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在 《艺文指导要纲》中指出:“要以‘新京音乐院’和‘哈尔滨交响乐团’为中枢母体,联系全满各音乐机构,推进建立全满的音乐联盟的工作。 ”并声言,“音乐之重要,在于各种场合都能显示其政治性。无论是宗教音乐的传播还是大众音乐的普及,都应使其纳入国民音乐总体建设规划之中,以期音乐与政治的紧密结合。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东北的音乐发展走上了畸形之路。
马颖介绍,日伪统治者认为歌曲起到的社会作用很大,因此对音乐流行的控制非常重视。对于黎锦光作词作曲的 《夜来香》这类旋律缠绵婉转的歌曲流行起来,日本人不会加以干涉。对于《何日君再来》以及“满映”拍摄侮辱、歪曲中国人民形象的几部电影中,由日本歌手山口淑子 (李香兰)、渡边浜子演唱的插曲《白兰之歌》、《支那之歌》、《苏州夜曲》等“满洲新歌曲”,日伪当局更是认为效果很好,大加鼓励。
日本殖民者还在东北大力推行 “新满洲音乐”,在课堂上强制教师教唱《向满洲进军》、《满洲姑娘》等为日伪政权歌功颂德的歌曲。
但对有反满抗日嫌疑的歌曲,日伪当局采取的态度是必须禁唱。 《满江红》、《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歌曲都列入了禁唱的黑名单。后来,日伪当局惧怕东北民众反抗到了草木皆兵、神经质的程度。他们认为歌曲《五月的风》中的“五月”暗指革命风暴,歌词中的“鸟儿、云儿、花儿”暗指东北三省的三千万同胞;认为歌曲《金丝鸟》暗示东北民众想要冲出牢笼。
压迫不能阻止心底的歌声
在日伪统治下,仍有不少爱国音乐家利用音乐活动与敌人明争暗斗,还培养了一批音乐骨干。
有的音乐教师还利用一切时机教唱热爱祖国和表述怀乡之情的歌曲,如《可怜的秋香》、《送别》、《真善美》等,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五月的鲜花》曲作者阎述诗这期间创作了三幕歌剧《梦里桃源》,描写青年痛恨黑暗社会,向往平等自由、没有剥削战乱的极乐世界。他还创作、翻译、改编了 《又一次落去的太阳》、《玛莎睡在冰冷的地方》等歌曲,来宣传抗日思想。
音乐家叶长春在哈尔滨中学任教时,拒绝教唱日伪规定的曲目。他教学生唱《满江红》、《苏武牧羊》,还教唱从关内传来的 《渔光曲》、《夜半歌声》、《卖报歌》等进步歌曲。在课堂上,他经常用演奏二胡躲避校长的检查。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参与口琴社活动。叶长春的一系列爱国活动引起日伪的注意。 1937年,他被开除,但依然一边以代课教师身份维持生计,一边参加爱国音乐活动。
音乐家刘忠当时也是音乐教师,他经常把中国古诗词谱写成歌曲,相信能影响学生坚定“正义必能战胜邪恶”的信心。除此之外,他还参加了不少进步音乐组织,通过演唱进步的中外歌曲,抓住一切时机表达亡国之恨和民族气节。(记者 张昕)

| 相关专题 |
| · 专题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