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红
2018年07月30日08:09 来源:北京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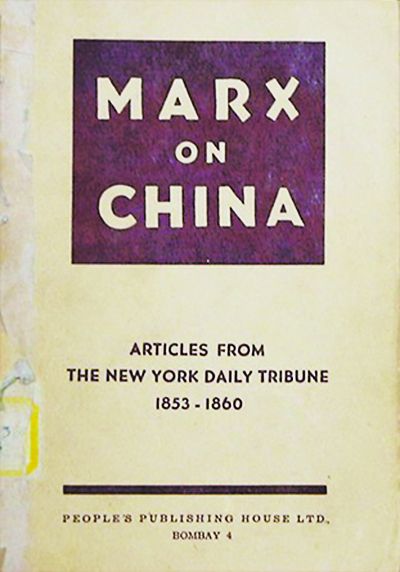
《马克思论中国》英文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通讯,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一定程度上,“中国”事物以及话题是马克思文本群、思想史、革命斗争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观”丰富了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一生中至少有151件作品(不含译作、读书笔记)、800多处文字直接论及中国。这些“论中国”的作品是马克思各时期、各领域、各体裁文本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对“中国”的关注经历了由“零星提及”到“集中论述”再到“补充深化”三个阶段。这一过程与马克思思想的转变、创立的学说和进行的实践密切相关。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世界观的变革,使得马克思从西方思想史中的“文本中国”印象走向了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现实中国”的关注。 马克思的“中国观”与其对“中国”乃至东方社会的阅读史密切相关,是在扬弃其他思想家的“中国观”以及与资产阶级报刊的倾向性报道斗争等中逐渐生成的。他不仅用很多称谓来指代“中国”,还根据国际事务中的中国角色,对中国的地域和物品、人物及其类型化的人以及中国在一些历史事件中的表现进行了评述,展示了中国停滞与变革、专制与自由等多维侧面。在具体事实描述的基础上,马克思根据“共产主义”世界历史趋势,阐述了中国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马克思的中国论述既充满着感情色彩,又积淀着理论支撑,对“世界形势变化中的中国”有着持续的关注,也生成了认识的变化和观点的深化。这也丰富了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所组成的整个理论体系,开启了“中国研究”的科学社会主义学派,奠基了理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中国”贯穿于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生涯始终
报人马克思一生创办、主编、协办、指导、供稿报刊,并有大量专论报刊的文章,还通过报刊来斗争和开展革命工作。马克思第一次论及“中国”的文章暗讽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严苛和不合理。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主要出自两人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马克思交往时间最长、发表“论中国”最多的报纸则属《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未署名而发表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马克思第一次以“中国”为标题的长文。他在该报上共发表专论“中国”的文章18篇,其中,《鸦片贸易史》和《新的对华战争》各分2、4次发表。马克思通过此报强烈谴责了英国、俄国等殖民主义国家的侵华实质,深刻剖析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热情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马克思从1851至1862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12年间,发表了约47篇“论中国”的文章,年均3.9篇。可以说,马克思“论中国”贯穿《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生涯始终,且为该报提供了重要的关于“中国”的讯息。显然,马克思发表在日报并被周报和半周报以及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宪章派左翼机关报周报《人民报》等其他报纸所转载、摘引的“论中国”文章较客观地传播了中国形象,并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家庭生活中也浸润着中华文化元素
马克思家庭生活中也浸润着中华文化元素,以家中成员的称呼为例,大女儿和小女儿的昵称均与中国有关。1863年12月15日,马克思给大女儿燕妮·马克思的信中在末尾说:“代我吻所有的人,特别是多多吻中国皇帝。”1864年7月4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中国皇帝和他的伙伴向你问好。”这里的“中国皇帝”就指大女儿燕妮·马克思,她甚至被称作“中国皇帝奎奎”(Qui-qui)。1868年1月1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最后说:“你若能在本月16日给杜西寄一团棉线,我将非常感谢。这一天是她的生日,而这个小骗子喜欢一切中国式的礼节。”“杜西”和“小骗子”指的是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1869年4月26日,《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所用的称呼为“我亲爱的小古古”(little Quoquo)并在最后说“再见,我的小古古。”可见,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在家里被戏称为“中国的皇太子古古”(Chinese Prince Quo-Quo)。在马克思家人的信件中,这些称谓经常使用,如1867年5月8日,卡卡杜(Kakadou,“白鹦鹉”之意,马克思二女儿劳拉·马克思的昵称)致信马克思说:“我确信暂时摆脱一下人们习惯称作‘家庭’的这个古怪的东西,摆脱一下‘古古’、裁缝等等大概别有一番情趣”,马克思对大女儿“Di”的称呼,可能是从中国皇帝“帝”的发音而来,而大女儿“Qui-qui”和小女儿“Quo-Quo”,或许是“格格”或“阿哥”的变音。 19世纪初期的欧洲报纸,常常介绍中国风物,作为逸闻趣事的清宫称呼和事物也被传播到国外。知识渊博、爱讲故事、善取外号的马克思更是为撰写中国问题的著述,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与政治有较多了解,他在“论中国”的文章中提到的中国“皇帝”就包括嘉庆(1760-1820,1795-1820年在位)、道光(1782-1850,1821-1850年在位)等,其中指涉“咸丰”(1831-1861,1850至1861年在位)的次数最多。可见,欧洲“中国热”对马克思有所影响,而他对中国事物也充满兴趣。在晚年研读民族学著作时,马克思又接触到了中国的一些材料,如1881年8月底至9月,还阅读并摘录了法国传教士埃·雷·于克(即“古伯察”)的《中华帝国》一书。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微信“扫一扫”添加“学习大国”

微信“扫一扫”添加“人民党建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