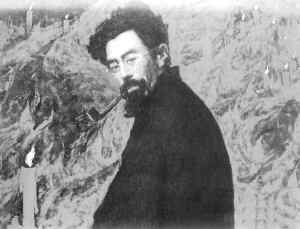
在聞一多48年的生命歷程中,約有40%的時間生活在北京(北平),前后達19年,相當於他在另外兩個居住時間較長的地區,故鄉湖北浠水(10年)和雲南昆明(10年)之和。這19年中從1932年至1937年的“清華六年”,則是成就聞一多學者身份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時間段。
清華六年,作為“新月派”詩人和英美文學學者的聞一多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而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學者的聞一多漸漸得到了學界的認可。
聞一多的北京(北平)19年,與清華大學及其前身清華學校有著不解之緣。
1912年冬至1922年夏,他在清華學校學習十年,之后放洋赴美留學。1925年歸國后,曾與徐志摩、朱湘等友人一起熱心倡導新詩格律化運動,在南京、武漢、青島等多地高校任教。1932年8月,聞一多接受了母校國立清華大學的聘請,回到闊別十年的清華,任中國文學系教授。自此直至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隨校南遷,前后6年聞一多一直在清華園內筆耕與舌耕,生活在北平這座文化古城中。
心情愉悅進清華
聞一多的“北平六年”其實也就是他的“清華六年”,而這六年又正值清華大學的一段“黃金時期”。清華大學的前身,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創辦的留美預備學校,1925年增設大學部和研究院國學門,逐漸改辦為普通大學,1928年正式更名“國立清華大學”。
由於各方政治勢力的明爭暗斗,清華大學經歷了多輪校長風波。直至1931年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任命梅貽琦為校長。梅貽琦就任后,專心辦學,清華大學漸入穩健、快速發展的軌道,由一所新辦大學,很快成為國內外知名學府。他的那段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就是出自他的就職典禮上的演說。
梅貽琦是清華出身的直接留美生,1915年回到清華學校任教,與聞一多有師生之誼。他到任8個月后即向聞一多發出中國文學系教授和系主任(聞未就)之聘,可見他對聞一多的知遇之情。
而聞一多在這樣的時候,這樣的背景下進入清華大學,無疑是會得到充分的尊重,是心情愉悅的。
“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環境”
清華大學及其前身清華學校由於有大筆的庚款支持,財力雄厚,辦學經費一直十分充裕。
在清華改辦大學之初的1925年,其生均經費為北京大學的4倍。梅貽琦撐校后,利用充裕的辦學經費,增建校園建筑,規定每年圖書儀器的購置經費,應不少於清華總預算的20%,還大幅提高教授的待遇。聞一多的月薪為340元,1936年度提高到380元——這是相當高的待遇,據學者陳明遠的研究,上世紀30年代“北平一戶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費平均隻需要30元左右”。
1934年10月,聞一多舉家遷入清華新建的西式教授宿舍新南院72號。據聞黎明、侯菊坤著《聞一多年譜長編》介紹,這是“新南院三套最大的寓所之一,有臥房、書房、客廳、餐廳、儲藏室、仆役臥室、廚房、衛生間等大大小小14間。電燈、電話、電鈴、冷熱水一應俱全”。他的“書房寬敞明亮,四壁鑲以上頂天花板的書櫥,窗下是書桌”。這裡是他“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環境”。
聞一多“北平六年”孜孜矻矻的“樂業”,與這樣豐厚的收入,這樣高起點、高水平的“安居”,顯然是分不開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