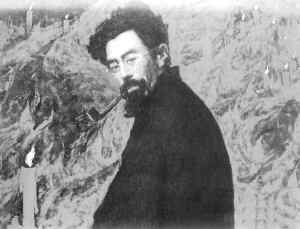
在闻一多48年的生命历程中,约有40%的时间生活在北京(北平),前后达19年,相当于他在另外两个居住时间较长的地区,故乡湖北浠水(10年)和云南昆明(10年)之和。这19年中从1932年至1937年的“清华六年”,则是成就闻一多学者身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段。
清华六年,作为“新月派”诗人和英美文学学者的闻一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学者的闻一多渐渐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闻一多的北京(北平)19年,与清华大学及其前身清华学校有着不解之缘。
1912年冬至1922年夏,他在清华学校学习十年,之后放洋赴美留学。1925年归国后,曾与徐志摩、朱湘等友人一起热心倡导新诗格律化运动,在南京、武汉、青岛等多地高校任教。1932年8月,闻一多接受了母校国立清华大学的聘请,回到阔别十年的清华,任中国文学系教授。自此直至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随校南迁,前后6年闻一多一直在清华园内笔耕与舌耕,生活在北平这座文化古城中。
心情愉悦进清华
闻一多的“北平六年”其实也就是他的“清华六年”,而这六年又正值清华大学的一段“黄金时期”。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增设大学部和研究院国学门,逐渐改办为普通大学,1928年正式更名“国立清华大学”。
由于各方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清华大学经历了多轮校长风波。直至1931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梅贻琦为校长。梅贻琦就任后,专心办学,清华大学渐入稳健、快速发展的轨道,由一所新办大学,很快成为国内外知名学府。他的那段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出自他的就职典礼上的演说。
梅贻琦是清华出身的直接留美生,1915年回到清华学校任教,与闻一多有师生之谊。他到任8个月后即向闻一多发出中国文学系教授和系主任(闻未就)之聘,可见他对闻一多的知遇之情。
而闻一多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背景下进入清华大学,无疑是会得到充分的尊重,是心情愉悦的。
“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环境”
清华大学及其前身清华学校由于有大笔的庚款支持,财力雄厚,办学经费一直十分充裕。
在清华改办大学之初的1925年,其生均经费为北京大学的4倍。梅贻琦撑校后,利用充裕的办学经费,增建校园建筑,规定每年图书仪器的购置经费,应不少于清华总预算的20%,还大幅提高教授的待遇。闻一多的月薪为340元,1936年度提高到380元——这是相当高的待遇,据学者陈明远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
1934年10月,闻一多举家迁入清华新建的西式教授宿舍新南院72号。据闻黎明、侯菊坤著《闻一多年谱长编》介绍,这是“新南院三套最大的寓所之一,有卧房、书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大大小小14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一应俱全”。他的“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镶以上顶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这里是他“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环境”。
闻一多“北平六年”孜孜矻矻的“乐业”,与这样丰厚的收入,这样高起点、高水平的“安居”,显然是分不开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