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陳獨秀:一位悲情的革命家(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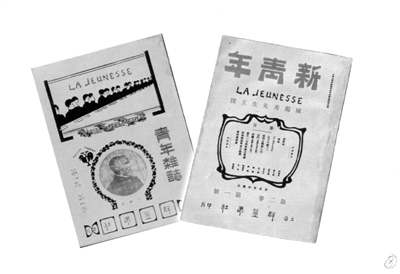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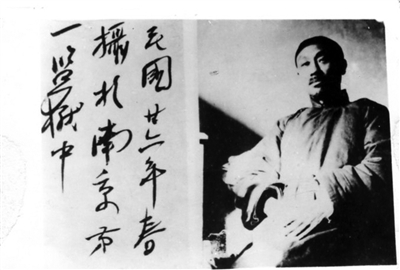
革命的成與敗
大革命的失敗,最關鍵的因素是中共沒有掌控武力,沒有建立自己的職業黨軍,這確是莫斯科直接指導的結果。
1927年春夏,國民黨清黨反共,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國共合作關系宣告破裂。國民黨隨后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共產黨則轉入地下。對中共來說,大革命已經失敗。革命失敗,責任誰負?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應負而不負,隻好讓陳獨秀“背黑鍋”,當替罪羊,將全部責任加諸陳獨秀一身,並命名為“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陳獨秀深感冤屈卻無處申訴。直到改革開放以后,學界才開始為陳獨秀翻案正名。然而翻案正名之路極為艱難,唐寶林先生直接參與了這一過程。這部書可以說是唐寶林先生為陳獨秀翻案正名而作,書前還專門交代了三十年來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
筆者充分肯定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重要意義,更敬佩唐寶林先生在書中為陳獨秀正名所作的種種努力。不過,翻案與正名的工作,總以原案、原名為“對話”對象。而原案、原名不過是當時出於政治需要而下的政治結論,並非基於學理的嚴謹判斷。亦因為此,要以嚴謹的學理去“証偽”或者“証實”那些政治結論,並非易事。更關鍵的是,翻案性的研究,其視野也難免為原案、原名的“問題意識”所牽引、所拘囿,因此而執著於“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與《汪陳聯合宣言》之類的討論,將問題的著眼點放在了討論誰應對革命失敗負責,而漠視了大革命更豐富的面相。無論是官方史學,還是翻案史學,對整個大革命歷史的研究,長期被“失敗史觀”所籠罩、所遮蔽,而看不到大革命其實也有相當成功的面相與經驗。海外學界的相關研究雖不為“左傾”、“右傾”所牽引,但當他們立足於探討1949年革命成功的因素時,更多注目於延安時期,而對陳獨秀時期在中共歷史上的重要意義同樣低估了。
我們評價作為中共早期領導人的陳獨秀,不可不對整個中共早期的歷史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觀察與定位。在1921-1927這短短的六年時間裡,中共成長為一個擁有近5.8萬黨員,3.7萬團員的組織,還有在其領導下的290余萬工會會員、900余萬農會會員和15萬童子團,其組織觸角輻射到全國大部分地區和各階層民眾。從工、農、學,到青、少、婦,如此范圍廣泛、規模宏大的“群眾”,在短時間內被納入到現代政黨的組織體系中並被有效動員起來,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共由一個知識分子的小團體,迅速成長為一個全國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視的革命力量,並奠定了群眾運動的基本模式與路徑,積累了豐富的策略、經驗與技巧。另如中共早期組織、宣傳的高超技巧,令同時期的國民黨、青年黨望塵莫及,自嘆不如。在大革命時期,國民黨的地方組織幾乎為共產黨人所“包辦”。在1926年初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后,大約90%的國民黨地方組織實際處於共產黨的控制之下,以至於中共中央可以直接向國民黨各省市黨部下發訓令。這個時期國民黨的輿論宣傳,實際也為中共所主導。應該說,陳獨秀時期,中共在組織、宣傳與群眾動員方面是相當成功的,相對於國民黨、青年黨具有明顯優勢,並一直保持和延續下去,成為中共革命最終成功的重要因素。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中共在組織、宣傳與群眾動員方面的強大優勢,威脅到了國民黨的生存,使國民黨人深懷恐懼,進而武力清黨反共。
長期以來,我們將大革命的失敗,歸咎於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對國民黨的妥協退讓。通過唐寶林先生的書,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這些妥協退讓確實大部來自莫斯科的指示。其實,今天我們尚可討論的是,大革命的失敗,多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共對國民黨妥協退讓造成的,如果不妥協不退讓就一定能確保大革命成功?抗戰爆發后,國共第二次合作,實際上就是以中共妥協退讓為前提的,正是承認三民主義,承認蔣介石的領袖地位,承認國民黨的執政黨地位,才能與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維持兩黨關系至抗戰勝利。再如指責陳獨秀時期沒有搞土地革命,其實,北伐時期,在沒有土地革命的情況下,能將幾百萬農民發動起來,反証土地革命未必是動員農民必不可少的要招。抗戰時期,中共從激進的土地革命退回到溫和的減租減息,同樣取得了很好的動員效果。
大革命的失敗,最關鍵的因素是中共沒有掌控武力,沒有建立自己的職業黨軍。而這確是莫斯科直接指導的結果。蘇聯一方面援助國民黨建立黃埔軍校,建立革命武裝,另一方面卻指導中共走十月革命路線——就是動員工農群眾,積蓄革命力量,等待適當時機,在大城市暴動,從而一舉奪取政權。上海的三次武裝起義以及之后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以及秋收暴動等,均是採取城市暴動型革命的路徑。中國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確實有成功的先例。只是當兩大革命黨競爭時,一黨有武力、有地盤,一黨無武力、無地盤,勝負不言而喻。毛澤東正是從大革命的教訓中悟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