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建忠
[摘要]從1952年10月至1972年8月,吳江縣先后收到三封與陳雲有關的來信。前兩封分別來自陳雲擔任負責人的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和秘書室,主要詢問吳江縣政府對陳雲姐姐陳星的接濟詳情,要求他們停止對陳星的接濟並稱此事以后由陳雲自行幫助解決﹔第三封為陳雲親筆所寫,請吳江縣鬆陵鎮將陳星留在該地的一些財物一概交公。這三封書信,涉及的事情雖小,卻反映出陳雲在處理涉及親情人情方面問題上的高風亮節,反映出陳雲既關心親人生活又時刻牢記黨員領導干部責任、嚴於律己的優良作風。
[關鍵詞 ]陳雲﹔書信﹔親情﹔嚴於律己﹔責任﹔吳江縣
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風暴席卷全國。從已經披露的案件來看,許多“蒼蠅”、“老虎”的違法違紀行為大多與其配偶、子女等親屬有關。有不少貪腐者在親情面前未能處理好始、微,感情用事,以至一發不可收拾。對於黨的干部和政府官員而言,如何處理親情,反映的不僅是個人的人格和人品,更反映出其黨性修養與責任意識的強弱。在這一問題上,陳雲處理家事的三封書信可以給我們帶來深刻的警示和啟發。
三封北京來信
1952年,吳江縣人民政府縣長楊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來信。信中寫道:“縣長同志,中財委陳主任的姐姐陳星,……據說縣政府對她很照顧,謝謝你們。……請你們查一下,每月接濟陳星多少錢(或多少米),已經接濟了多少次。陳主任講,現在補貼增加了,干部家屬不必再要公家接濟。請你們至 12月份起,即停發陳星的接濟費用,不必客氣。以后由陳主任自行幫助解決。盼你們即(及)早復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為“中財委辦公室”,時間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說的陳主任,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主任的陳雲,當時中央財政經濟工作的領導人。
接到來信,楊明感到非常突然,他十分清楚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對工作人員普遍實行供給制,而后實行包干制,雖然“現在補貼增加了”,但仍十分有限。而且,陳星當時雖然是一人生活,但畢竟年過半百,個人又沒有任何收入來源,而陳雲的家庭負擔也較重,是黨內高層有名的困難戶之一,要其“自行幫助解決”,實在非常不易。沒想到的是,一個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來了。信雲:“吳江縣長同志,我們於上月 27日寄去一信,請於 12月份起停發陳主任之姐在你縣所領的家屬優待費,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陳主任現在供給較前提高,所以提出應自己補助其姐。但究竟過去由縣政府補助多少,請即告知。並請即告處理情況,為盼!”這次的署名是“中財委秘書室”,時間是11月28日。這兩封信,雖然不是陳雲親筆所寫,但很顯然,表達的都是陳雲本人的意思。沒有陳雲的交待,一定不會有這兩封信函。這兩封信目前都存放在蘇州市吳江區檔案館。與這兩封信放在一起的,還有兩封信。一封是吳江縣的回信(或是底稿),寫於 11月24日,稍早於第二封信的寫作時間。另一封信是陳雲的親筆信,是代他姐姐給“吳江縣鬆陵鎮
革命委員會”的回函,寫於 1972年 8月 23日。信中說:“你們 1972年 8月 6日給我姐陳星的信收到。我姐姐正在病中,此事由我作主,如果我姐姐有另(零)星家具存在凌文英家中,可以都按凌文英財產處理辦法一概交公。專復並致敬禮!”
為何是吳江
陳雲為什麼會給吳江縣寫信,其姐姐為何會在吳江?
陳雲的出生地,按現在的說法,是上海市青浦區練塘鎮。實際上,在陳雲出生的 1905年,練塘鎮是隸屬於吳江縣的。陳雲的姐姐陳星與吳江的關系就更深了。她比陳雲大 8歲,於 1915年嫁給了練塘鎮協和昌南貨店的一個王姓職工。抗戰后期,陳星隨女兒一家來到吳江縣鬆陵鎮。先是租住在鎮上一周姓人家,后來改租到了鬆陵大戶人家的沈家花園裡。
陳星女婿曾在民國政府吳江縣保安團任下級軍官,吳江解放前夕,他們一家去了台灣,就陳星一人留在了吳江。 1950年 4月,陳星曾被接去北京,但因不習慣北京生活, 10月又回到鬆陵居住。
陳星在鬆陵並無固定工作和收入,女兒臨走時,留了一點生活財資給她,但並不多。新中國成立初期,陳雲曾通過當時蘇南行署的主要負責同志轉給陳星一些錢,以接濟她的生活。這位負責同志后來寫信給吳江縣政府,建議吳江給予陳星這位革命功臣的家屬以必要的幫助。吳江民政部門便從 1949年 12月起每月給陳星一定的大米接濟,到 1952年 11月接到中財委辦公室信函時止。其間, 1950年因陳星離開六個月,停發了半年。
第三封來信中提到的凌文英,是陳星離開吳江前的房東,亦即前述沈家花園主人的填房夫人,文革中因成分不好,房產將被沒收。有關部門在處理過程中因發現陳星把家具都留在了凌文英家的房子中,便去信陳星,詢問這些家具的處理辦法,不想收到了陳雲的親筆回函。
親情重要,但絕不能損害公家利益
陳雲夫人於若木在談到陳雲感情問題時,曾說陳雲有血有肉,也有家庭親情,這些方面,他還是很重視的。
這一點在陳雲給吳江的那封親筆信中體現得十分突出。這封信,一共就 70多字,其間有三次提到陳星,但沒有一次是直寫“陳星”其名,也不用“她”等來代稱。除第一次用的是“我姐陳星”,表明是為陳星的事情而來外,其余兩次都是一口一個“我姐姐”。這體現出的正是姐弟情深。
陳雲自小家境貧寒,父母勞作辛苦,更不幸的是,他兩歲喪父,四歲喪母,盡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顧,但畢竟和父母健在不一樣。年幼的陳雲一直由姐姐照看。
陳雲一直把照顧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國剛成立不久,他便托人給陳星捎錢接濟她的生活。 1950年 4月,又將陳星接到北京,以便可以更好地照顧她。在陳星重新回到吳江后,陳雲非常挂念她的生活。后來,陳雲還是把陳星接到了北京,給她養老。
本來,由地方組織給予開國功臣中有困難的親屬一些優待,於情於理都十分自然,但陳雲不這麼想。在第一次去信謝絕后,由於沒有收到回復他再次發信,重申這一態度!顯然,在陳雲的心中,親情重要,但絕不能為此損害公家利益。
陳雲的可貴之處還在於他在這一問題上能時時注意,處處自省。 1959年 6月至 1960年 9月,陳雲外出休養。根據需要,於若木一同前往。離京期間,於若木的工資由她單位的有關人員代為領出並幫助儲存了起來。待相關人員把這些工資交給於若木時,被於若木如數退回。原因是陳雲有交待,在陪他休息的這個期間她不能拿工資。
這就是陳雲。對姐姐嚴,對妻子嚴,但另一方面,又“自己補助姐姐”。情與理,公與私,一點不馬虎,一點不含糊。
貴在日常堅持
習近平曾深刻指出,在作風問題上,起決定作用的是黨性,衡量黨性強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參見《人民日報》2014年 1月 16日。)陳雲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中也說過:“不要以為自己能夠在會議上或稠人廣眾之前聲明擁護並舉手贊成黨的路線,就算遵守了黨的紀律,這是十分不夠的”﹔“一個真正能自覺遵守紀律的好黨員,就在於他能在實際行動和日常生活的每個具體問題上,表示出自己是堅決地遵守黨的鐵的紀律的模范。”(《陳雲文選》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139頁。)關鍵在“實際行動”,在“日常生活
的每個具體問題上”!他是這麼教育人的,也是這麼要求自己的﹔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早在 20世紀 30年代初,陳雲就開始擔任黨中央的領導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又是中央負責財經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對他而言,如果有私心為自己謀利,可以說很方便,但他卻從來沒有。這體現出他的高度自律和共產黨員的堅強黨性。而主動謝絕基層政府對自己家屬的優待,則體現出他的細心與認真。由於當時的交通條件十分有限,加上地方上的處理也有個過程,陳雲在一個月未能收到及時答復后又緊接著發出第二封信,體現出對這件事情的深切關心和認真負責到底的態度。
中財委辦公室秘書室代陳雲書寫的兩封信函,還在字裡行間流露出陳雲強烈的責任意識。這份責任,首先是他要自己承擔對姐姐生活的照顧之責。這是他的家庭責任。同時,陳雲更看重的,還是共產黨員克己奉公的自律之責和領導干部的帶頭之責。否則,他不會反復堅持,一再強調。習近平指出:黨員領導干部應做到“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際關系,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則辦,特別是當個人感情同黨性原則、私人關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必須毫不猶豫站穩黨性立場,堅定不移維護人民利益”。(《人民日報》2014年 3月 19日。)陳雲在這方面無疑是一個典范。
中國是個講究人情的社會,人在親情面前很容易迷失。陳雲的可貴,就在於他身上重情重義與嚴守紀律的和諧統一,在於他時刻牢記黨的領導干部的自律責任、帶頭責任、監督責任、教育責任和引導責任的高度自覺。陳雲不為親情而放棄原則,重情但絕不允許損害公家利益。責任、自律、認真,是陳雲處理親情問題時的方式,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
〔作者陸建忠,中共蘇州市吳江區委黨史工作辦公室副主任。〕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四期
相關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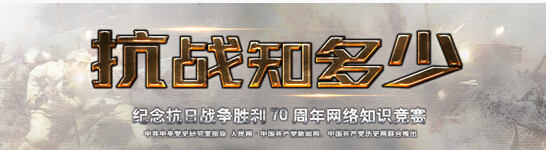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