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俊珺

|
常书鸿(油画)
克卫 作

|
||
1948年,常沙娜赴美国学习前夕与父亲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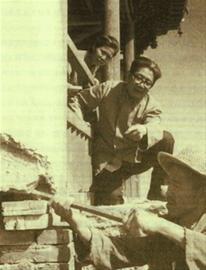
|
||
1954年,常书鸿在莫高窟指导工作人员维修栈道。

|
||
1991年,常沙娜与父亲在北京合影。
“痴”,在这个时代或许已属罕见,甚至常常和“傻”联系在一起,为人不屑。
其实,无论是搞科学研究,还是从事艺术创作,干事业总需要一些“痴”的精神。这种“痴”,是一种超脱世俗的追求,是一种专注忘我的境界。
常书鸿就是这样一个“痴人”,他痴守莫高窟50年,几乎把一生都交付于他所痴迷的敦煌,无怨无悔地守护着这座人类的艺术宝库。
午后的北京,记者如约走进常沙娜的家,窗前绿植环绕,墙上挂着她与父亲常书鸿的合影,从青春到年迈。
常沙娜从柜子里取出一本画册,那是她年少时跟随父亲在敦煌莫高窟里临摹的画作集。
“你看,这是我跟父亲的学生在159号洞窟临摹的普贤菩萨图,那时候我14岁;这是我17岁时,在290号洞窟临摹的飞天图……”
熟悉的画面一页一页翻过,如今已82岁的常沙娜眼里放射出青春的光芒。她说,看着这些画,耳畔仿佛又响起了莫高窟大佛殿檐角叮叮当当的铃声……
痴迷
从此,中国画坛少了一名优秀的画家,但敦煌有了最可贵的守护者
解放周末:您跟随父亲在敦煌生活了多长时间?
常沙娜:我12岁那年跟着父母去了敦煌,一直到17岁。
解放周末:那段时间,父亲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常沙娜:父亲那时候特别忙,常常顾不上我,但我喜欢跟着大人们进洞窟,看他们工作。后来父亲就抽空给我讲壁画里的故事,教我画画的基本功,让我跟着大人们一起临摹。一个人在洞窟里时,我还会对着墙上的“飞天”唱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长亭外,古道边……”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解放周末:您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工艺美术设计家、教育家,还编著了《中国敦煌历代服饰图案》、《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等,这一切是不是都与年少时在敦煌的经历有关?
常沙娜:是的,父亲给我起名“沙娜”,好像就注定了我们全家与沙漠的不解之缘。
1931年,一个女孩在法国里昂出生,父母借里昂的护城河名“Soane”,为她取名“沙娜”。
常沙娜的童年记忆都在巴黎。每逢周末,家中的小客厅就成了中国留法学生的艺术沙龙,徐悲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这些日后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闪耀的名字,她从小就熟知。而在当时,最令这些人羡慕的,是她的父亲常书鸿。
那时,这位只有三十岁出头的浙江青年已留法近十年,是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劳朗斯最得意的学生。他的画作多次跻身法国国家沙龙展,连续四年斩获三枚金奖和两枚银奖,更有作品被收入法国国家博物馆,前途不可限量。与此同时,常沙娜的母亲也在巴黎学习雕塑。这个艺术之家的生活,如轻快的手风琴般,安定舒适。
一天下午,常书鸿像往常那样溜达到塞纳河畔的旧书摊淘书。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册子吸引了他的目光,里面全都是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盗宝时所拍下的图片。常书鸿被迷住了,他第一次知道敦煌在自己的祖国,痴痴地捧着书,直到收摊也舍不得放下。见这个年轻人一连几天都来看这本书,摊主告诉他,吉美博物馆里就有敦煌的艺术品。
从吉美博物馆回来,常书鸿难掩兴奋之情,他激动地对妻子说,自己过去一心倾倒于希腊、罗马的西洋文化,竟不知道自己的祖国还有这么一座不可思议的艺术石窟,真是数典忘祖,不知如何忏悔才好。
“从那天起,敦煌就成了父亲魂牵梦绕的地方。”常沙娜说。
1936年,常书鸿拿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聘书,踏上了回国的列车。
等待他的,并不是梦想中的敦煌。回国后的第二年,抗战爆发,常书鸿刚刚把妻子与常沙娜接回国,一家人就被裹挟进了长达4年的颠沛逃亡,直到他在重庆谋得了一个教育部下辖的职位,一家人才安定下来。不久,长子于嘉陵江边出生,取名嘉陵。
1942年的一天,一场“战争”突然在这个平静的四口之家爆发。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成立,在梁思成、徐悲鸿等人的联合举荐下,常书鸿成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
“母亲对父亲说,你疯了!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沙娜也不能去,她还要上学。她对我说,我们好不容易不必再逃难了,现在你爸爸又要到甘肃去,那里连房子都没有。”常沙娜还记得母亲当时的震怒。
不想去敦煌的,何止是他的妻子。在兰州招募工作人员时,“敦煌”二字几乎无人问津。经过苦苦劝说,一名曾在北平艺专就读的学生终于答应跟随常书鸿去敦煌。后来又想方设法招来了文书和会计,一行6人身穿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的毡帽,顶着早春刺骨的寒风,开始了敦煌之行。
临行前,梁思成送给常书鸿四个字:“破釜沉舟!”
从此,中国画坛少了一名优秀的画家,但敦煌有了最可贵的守护者。
 |
